1
科学家角色是科幻小说的大脑,犹如蝙蝠侠之于正义联盟。即使暂不考虑被公认为科幻小说之鼻祖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初版,1831年修订),按照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一书中认为的那样,将科幻小说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小说里的幻想旅行作品,我们也能在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冒险中发现科学家前世的幻影。撒莫萨塔的卢奇安(120-190)在其《伊卡洛墨涅波斯》中,想象主人公将鹰的翅膀绑在身上,飞向月球,进而飞入太阳,直达天界面见宙斯:这一危险的飞跃体现了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前往陌生国度的信念与勇气。

不过,在将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和代达罗斯们援引为科学家的象征之前,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技艺与今日所谓之“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不仅是因为以物理学和仿生学知识来看,用蜡和羽毛制作会飞的翅膀有多么不靠谱,更因为“科学”与“科学家”之概念的生成与建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于一些强硬的批评家来说,“科学”这一术语毕竟是定义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核心问题,所以要避免因概念不清产生的混乱,必须将代达罗斯们的故事从科幻小说的历史中排除出去。
科学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晰了然的。譬如,现代医学的诸种理念早在盖伦的时代便暗藏萌芽,但那时它还在经受交感巫术思维的侵扰,必须要等到千年之后,对人体的解剖破除万难成为一门学问,医学才有脱胎换骨之可能。在现代科学漫长的分娩过程中,诞生了占星家、炼金术师和药剂师这样的过渡产物: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贡献,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与代达罗斯仍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变化发生在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之后:他的经院哲学将基督教义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理性知识体系,这是一件一件艰巨但伟大的任务。这一创举的重要之处在于,经院哲学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认为,可靠的知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所有的感觉都必须经历演绎推理的仔细审查和归纳实证的检验——我们对现代科学的认识便滥觞于此。布莱恩·阿尔迪斯坚定地认为科幻小说真正起始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也正是因为在19世纪,“科学”一词才获得了它的文化性认可。这样一来,代达罗斯们就和科学家划清了界限:他们是一群富有实干精神的优秀手艺人,敢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探索未知或创造可能,但手艺和科学之间终究存在着可悲的障壁。对科学的定义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是可以系统学习的。一个小学生认真而循序渐进地学习数学和物理学,倘若他足够聪慧,完全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爱因斯坦的接班人;而一门技艺总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那就是失传。技艺往往过分依赖手艺人的天分、勤恳、热爱以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而且越是精妙绝伦的技艺,人们就越是愿意用后继无人的悲剧结局来彰显其卓越性:而一旦如此,它就只能在神话的领域中辗转流离。无论是代达罗斯的翅膀也好,偃师的人偶也罢,它们更多体现的是古人对个人能力的憧憬和仰慕,和今日的科学相比相距甚远。若说代达罗斯与阿瑟·克拉克们笔下的科学家主人公们有何共同点,那便是智慧、信念与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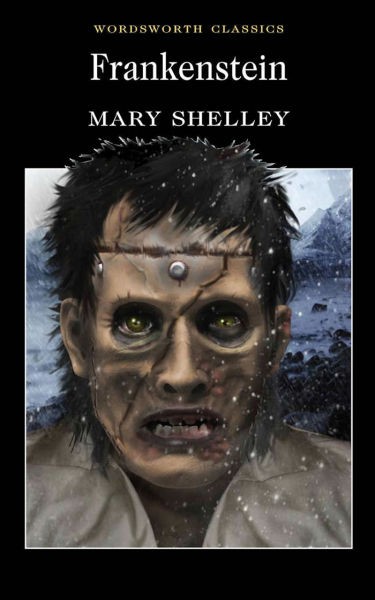
2
如果我们要讨论科学家,就必须先弄清楚自己真正在讨论什么。贸然使用“科学家”这个今天听起来习以为常的词语是件危险的事,因为它和“科学”一样,都是相当年轻的词。斯特凡·科里尼(Stefan Collini)在为C.P.斯诺《两种文化》一书之的再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学家”一词最早在1834年作为“艺术家”的对应而被提出:
由于缺少一个特定词来称呼“物质世界知识的学生”,这给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造成了很大困扰。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聪明的先生提出,可以借鉴“艺术家”一词,创造“科学家”这一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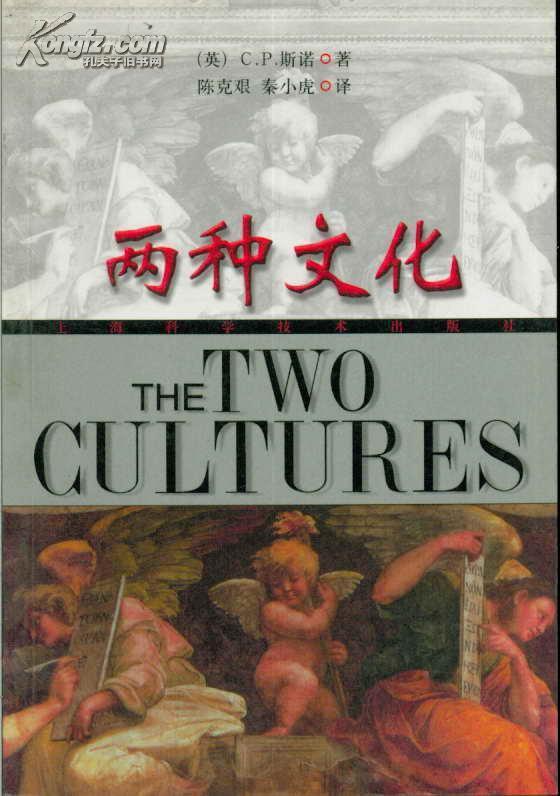
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弗兰肯斯坦们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斯《化身博士》(1886)中亨利·杰基尔们悲惨的遭遇中多少总带些宗教式的训诫意味,因为他们胆敢用自己脆弱的心灵触碰广袤而深邃的不可知领域;但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在利尔·亚当的《未来的夏娃》(1886年)、加雷特·P.赛尔维斯的《征服火星》(《纽约晚报》1898年1月号,1947年出版)、雨果·根斯巴克的《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连载于《现代电气》1911年4月号至1912年3月号;1925年出版)等作品中,能够洞察真理的科学家,或者拥有改造自然环境技术的工程师们开始以更加正面、积极的形象在科幻作家笔下抛头露面了。我们不难推测这一转变的诱因:像路易斯·巴斯德这样的科学家或者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大发明家开始被世人崇拜(一个有趣的事实:爱迪生与特斯拉和赫拉克勒斯这样的半人半神一样,都成为了游戏FATE GRAND ORDER中的从者,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造神术),昭示着科学家逐渐成为了一种足以令普罗大众憧憬的角色。因为拥有知识和技术,以及将它们当作利剑的勇气与信心,赛勒斯·史密斯就与野蛮人柯南区分开来了。不过,随着后世科幻小说内涵的拓展与延伸,人们也会发现要区分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一部严谨清晰的奇幻小说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可能要远超过那种胡乱堆砌太空舰队、星际大战的平庸科幻。

科学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相生相伴,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过于自信的观念:当人们发现物理学的解释范畴正在不断扩大时,便产生了一种元叙事。这种元叙事认为,世界是可以被彻底认识、彻底阐释的。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理解整个世界,凭数学和公式计算出这世界上所有的真理和可能性。这样一来,所有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激情和感伤,艺术的纤弱与优美,悲剧的崇高和诗歌的庄严,便通通被这样一种元叙事遮蔽了。这种想象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1951)。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种元叙事随着牛顿的大厦一齐垮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文化分界:这就是C.P.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一概念是斯诺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出的)。科学与艺术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关系,各自凭借其理性严谨与浪漫冲动占据一级,甚至彼此制衡抗争。当然,这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后果,并非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且没人能保证“科学”与“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度发生变化——卡尔·波普尔对证伪的反复强调就颠覆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
3
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科学家曾经无条件地接受着来自普罗大众的憧憬,但人们随即意识到,自己很难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我们似乎难以绝对公允地评价梅耶、冯·布劳恩和奥本海默们的是非功过,但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极大的恐怖。这种恐怖很快便颠覆了人们对科学家的盲目崇拜,并再次将弗兰肯斯坦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召唤回来。
尽管地位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新一代的疯狂科学家们和前辈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心如磐石,意志坚定。弗兰肯斯坦因为纯粹的好奇和无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而新一代的邪恶科学家们则将盒子捧在手中,满世界倾倒灾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凡尔纳的《蓓根的五亿法郎》(1879):书中刻画了针锋相对的两位科学家——善良的沙拉塞恩与邪恶的舒尔策。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反复书写这种正邪对抗的故事。
我们还能列举出很多这种形象鲜明的邪恶科学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2003)中的“秧鸡”,伊藤计划《虐杀器官》(2007)中的约翰·保罗,或者阿兰·摩尔《守望者》(1986)里的法老王。这些危险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前辈(弗兰肯斯坦们或亨利·杰基尔们)相比,摒弃了虚弱、犹豫和神经质的性格弱点。他们都是尼采的后裔,拥有偏执的神经、冷酷的意志和永不动摇的信念,而且不必再承受世间一切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制约。更重要的是,如果弗兰肯斯坦用尸块和电气制造了科学怪人是种荒诞不经的想象,那么秧鸡在实验室里合成一种足以灭世的病毒则是完全可行的:任何读者都会明白哈利·波特的魔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真,但有时很难确定科幻小说中令人发指的恶行究竟会不会在现实中重演。这就导向了科幻小说的另一重功能:它不仅仅是一种未来学的想象,更是一种启示录式的寓言书写。
消费主义产生过度的,泛滥的爱(一种最直接,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偶像崇拜和粉丝经济);这些危险科学家们代表的则完全是它的反面,因为要与这些病态的,过量的爱意对抗,就要拿出同等分量的憎恨,以此来中和这个被愚蠢地扭曲了的世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体现为对当下无穷无尽的恨意,一个割裂开的时间,一种弥赛亚式的信念。这就是菲利普·迪克《血钱博士》(1965)中的布鲁兹盖德。同样的道理,《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中的保护伞公司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两败俱伤式地摧毁世界,看上去毫无逻辑可言,但也不必过于惊异:这家公司掌握着匪夷所思的跨时代技术,但毕竟在本质上个是宗教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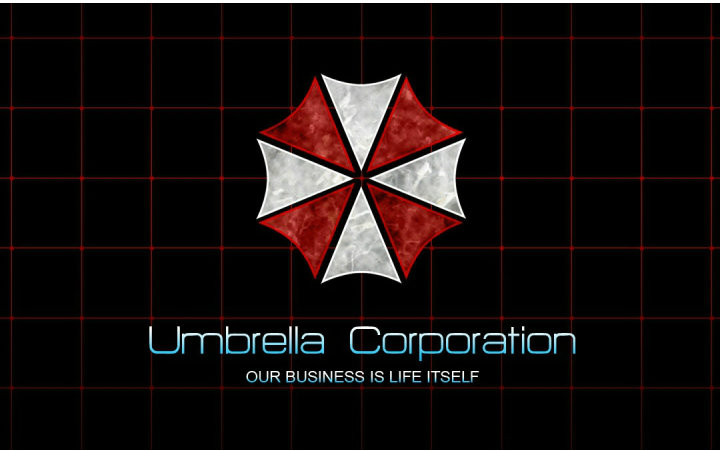
4
另一类科学家呈现出的则是悲剧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遭到外力的扭曲,被大财阀和大独裁者们野蛮地剥下头顶的神圣光环,最终与他们制造的机器沦落到同等地位。布尔加科夫的《不详的蛋》(1925),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皆属此列。也有一些科学家属于“时运不济”的类型,譬如许地山《铁鱼底鳃》(1941)中塑造的潜艇发明家。
我们很容易从历史中追溯出此类科学家形象诞生的根源:斯大林时代政治对科学的粗暴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横行。这些小说以冷酷的姿态道出了一个事实:科学家的领地只有自己研究室内的那一亩三分地,当历史的洪流向前滚动时,他们太过软弱,没有那种独善其身的力量。
也同样因为这种软弱性,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些作品时,往往更集中于科学家背后的施暴者与加害者,身为主人公的科学家形象反倒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留给这些科学家们的出路并不多:要么在小说的结尾悲剧地自我毁灭,要么则像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
5
不过,在新中国科幻的最初阶段,科学家是直接以正面形象登场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那时,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地位得到了重视:这些人是聪明(而非天才)勤奋的优秀劳动者,和人民紧紧打成一片,所做所为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智尽忠。尤其在饱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科学的力量对发展工业和军事,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彼时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科幻小说大多遵循一种最基本的模式:一位好奇的青年/少年,身份可能是少先队员/记者,因公或因机缘巧合进入一座新农场/牧场/工厂,在那里见到了一位和蔼聪慧的科学家,并在科学家的带领下了解到了新技术是怎样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迟叔昌的《大鲸牧场》(1961)、《科学怪人的奇想》(1963),童恩正《电子大脑的奇迹》(1962)等皆属此类,不一一列举。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学家不仅仅是这些农场/牧场/工厂的核心人物:他们同时也勤恳地担任着导游和讲解员的角色,耐心地给主人公引路。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真正的科学家恐怕没有这么多闲暇时间;但这一设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向读者说明,科学家并不是一群闭门造车、与世隔绝的老顽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队伍中的重要成员,永远和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比如在郑文光《征服月亮的人们》(1955)中,对于探索月亮的科学家谢托夫教授来说,和少先队员们围坐在一起讲述自己的奇遇,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也是同样重要的工作之一。即使是那种因研究涉及绝对机密或者风险巨大而足不出户、遗世独立的科学家,也一扫霍夫曼们笔下那种阴郁可怖的形象,成为了一名为祖国默默奉献的勇士。这一点在叶永烈的小说《爱之病》(1986)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果科学家不必非要身处最前线也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他们身上的空间属性事实上也就被淡化了。
然而这些“完美的科学家”形象在科幻小说中是难以为继的。他们的人格太过完美,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几乎很难产生什么戏剧冲突。如果把他们当作主人公,小说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的独角戏舞台;如果让他们充任配角,在他们身上往往“解说”的职能压过了故事的职能,以至于他们的角色无法再唤起读者们的憧憬,只能让人觉得僵硬讨厌。所以很快,此类角色便很少出现了。张冉、夏笳、陈楸帆等新生代科幻作家笔下的科学家形象开始更加关注科学家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关注他们的生活、情感,以及心灵深处最为细小纤弱的那些裂缝;而像刘慈欣《三体》(2006)中罗辑和丁仪这样的科学家形象之所以有趣,则是因为刘慈欣特地让他们沾染了些玩世不恭的气味;“邪恶科学家”的形象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了。总的来说,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科学家们看上去更有趣些,尽量摆脱所谓“扁平人物”的刻板印象。不过有时我们也很难断言这种转变究竟是好是坏,因为科学家们很难再像从前那样“纯粹”了。
科学家的形象已经随着科幻小说的发展演化了近两个世纪。未来它又会发生怎样的演变?这一点我无法预测。但可以确信的是:人们对科学家形象的想象,绝不仅仅由科学决定。伊恩·麦克尤恩在《追日》(2010)中塑造的、毫无作为的猥琐科学家迈克尔·别尔德就是一个绝佳的新形象:他卑鄙的性格和失败的人生成为了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这一议题令人尴尬的暗喻。新的可能或许在第三世界,在广袤的黑非洲……笔者不才,只好等有识之士进一步挖掘了。
作者:钟天意,作家,独立书评人。尼古丁中毒的狼人学家。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科普中国APP)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