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塔伦·K·圣(Tarun K. Saint),独立学者、作家,出生于肯尼亚,自1972年起移居印度,主要关注印巴分治时期的文学与科幻小说,并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见证分治:记忆,历史与虚构》(Witnessing Partition: Memory, History, Fiction,2010)一书。此外,他曾编纂文集《布满伤痕的记忆:种族暴力与作家》(Bruised Memories: Communal Violenceand the Writer,2002),并与拉维坎特(Ravikant)共同编辑《翻译分治》(Translating Partition,2001)一书。他还与拉赫尚达·贾利勒(Rakhshanda Jalil)、德贾尼·森古普塔(Debjani Sengupta)合编了《回首往事:印巴分治,70年后》(Looking Back: India’s Partition,70 Years On,2017)。同时,他还是维克多·格兰茨出版社《格兰茨南亚科幻小说选》(The Gollancz Book of South Asian Science Fiction)第一卷(2019)与第二卷(2021)的主编。他与弗朗西斯科·沃尔索(Francesco Verso)合作主编的印意双语科幻小说选集《阿凡达:印度科幻小说》(Avatar: Indian Science Fiction)已于2020年1月面世。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早已重新定义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与生活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科幻小说也成为了这个时代新的现实主义。正如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预言的那样,一场想象中的大灾难正在降临,他在小说《雪》(The Snow,2018)中刻画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暴风雪,而故事的主人公恰恰来自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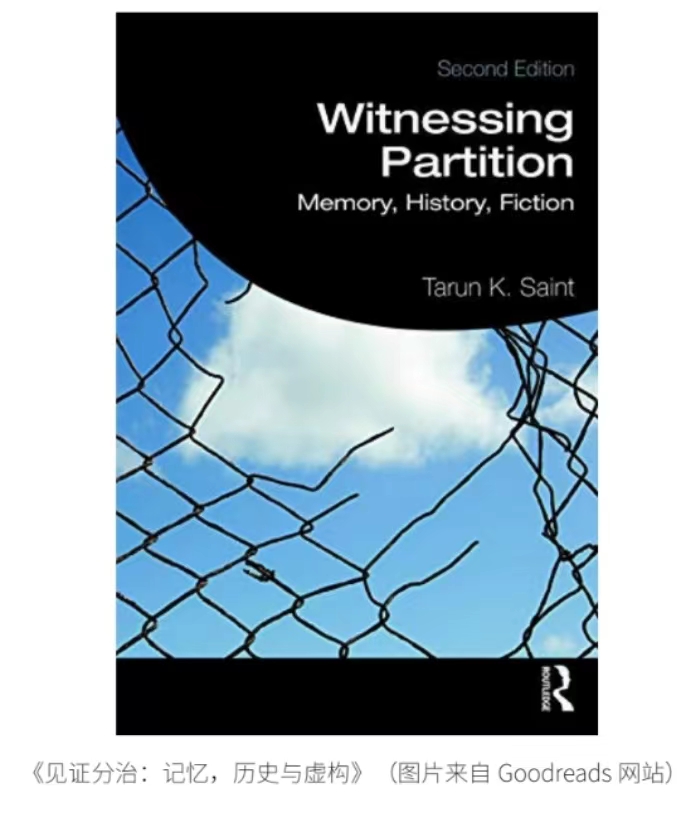
本文将介绍近二十年来印度科幻小说的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印度科幻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而离散1作家也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这些年的变化,科幻小说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目前来看,印度科幻创作正生机勃勃,而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科幻潮流,我们需要回退一步,追根溯源。印度最早的科幻雏形出现在19世纪,在一段“原型科幻”(proto-SF)时期之后,印度科幻终于在20世纪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在印度民族想象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值得一提的是,科幻的影响力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西孟加拉邦最为显著,而二者也正是印度殖民时代以来受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地区,其地方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
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2带来的抗议精神在印度影响深远,引导人们质疑以西方科技为基础的主流社会话语,并且通过强调本土知识,使人们认识到本地生态的敏感性,这些都影响到了印度科幻小说的创作过程。自1991年开始,印度经济加快了自由化进程,需要社会通过主流与通俗文学作出更加尖锐、批判性更强的回应。因此,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印度科幻新浪潮并非偶然。这种未来主义的愿景,往往建立在对全球化、消费主义、印度的“多数民族主义”(majoritarian nationalism)3的反思,以及社会和文化转型引起的集体性焦虑之上,并且从环境运动(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和对主流社会发展的批判中获得了推动力。
与此同时,讽刺的是,得益于自由化运动和经济改革,越来越多的国际出版社纷纷在印度开设分社,文学领域内出现了新的类型。这一时期科幻小说的两股新力量分别是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科幻小说《加尔各答染色体》(The Calcutta Chromosome,1996)和曼余拉·帕德马纳班(Manjula Padmananabhan)的科幻剧本《器官收采》(Harvest,1997)。这两部作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从不同角度传达出对科学和技术的怀疑。
这类对生态显示出强烈关切、带有鲜明的性别色彩和个人风格的小说,在本世纪初大放异彩,以帕德马纳班(Padmanabhan)的《逃》(Escape,2008)与《失踪少女之岛》(The Island of Lost Girls,2005)为代表。这两部反乌托邦小说探讨了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的社会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女婴出生率不容乐观。最终,主人公逃离了她出生的国家,摆脱了限制性政策和系统性的性别歧视,来到一个由女性管理的岛屿。某种意义上,尽管这座岛屿是她的避难所,但岛屿内部也有更复杂的政治因素在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关注这些主题的作者习惯使用地方语言,比如孟加拉语作者普雷门德拉·米特拉(Premendra Mitra)和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以及马拉地作者贾扬特·纳利卡(Jayant Narlikar),等等。
同时,在世界科幻领域,阿尼尔·梅农(Anil Menon)和范达娜·辛格(Vandana Singh)的知名度显然更高,他们不仅出版过长篇小说和个人短篇集,而且在许多著名科幻杂志上都发表过作品,将印度科幻带上了世界舞台。他们的作品有时带有一种离散的特质,梅农在回到印度浦那之前曾在美国担任软件工程师多年,而辛格在德里接受早期教育后在美国教授物理。

辛格的科幻小说收录在《自视为行星的女人》(The Woman Who Thought She Was a Planet,2008)和《模糊机器与其他故事》(Ambiguity Machines and Other Stories,2018)两本书里。此外,她还写了一篇推想小说宣言,收录于《自视为行星的女人》,概述了这一体裁的革命潜力。辛格始终抱着“如果……怎么样?”的态度,对印度的等级制度和被动接纳的世界知识体系提出质疑。《模糊机器与其他故事》中的《因陀罗网》(Indra’s Web)是她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书中虚构了一个名为“苏利亚网络”(Suryanet)的新型太阳能源网项目,以保障德里郊外的贫民窟——阿沙普尔地区(Ashapur)居民的生活。故事中,森林里的植物之间建立了一个网络,其灵感来自现实中植物之间传递的生化信号。同时,辛格围绕主人公寻求能源危机解决方案的过程,着重描写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与她祖母的关系。这篇科幻小说既借鉴了传统知识,也参考了当代生物学和物理学的研究。阿尼尔•梅农也写过两部科幻小说:《九十亿英尺的野兽》(The Beast with Nine Billion Feet,2009)和《我说的一半》(Half of What I Say,2015)。其中,前者的定位是青少年小说,叙事设定在2040年的印度浦那,传递出对性别问题的敏锐关注,其出版社“祖班”(Zubaan)有着女性主义背景。故事中一位遗传学家被迫逃亡,对他的家庭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他的女儿塔拉(Tara)。后者的灵感源自2011年的印度反政府抗议运动。梅农在这部推想小说中,虚构了一股代表人民力量,即名为“人民力量”(Lok Shakti)的势力,它在未来会向印度国家权力发起实质性挑战,以多种方式对形式化技术的局限性表达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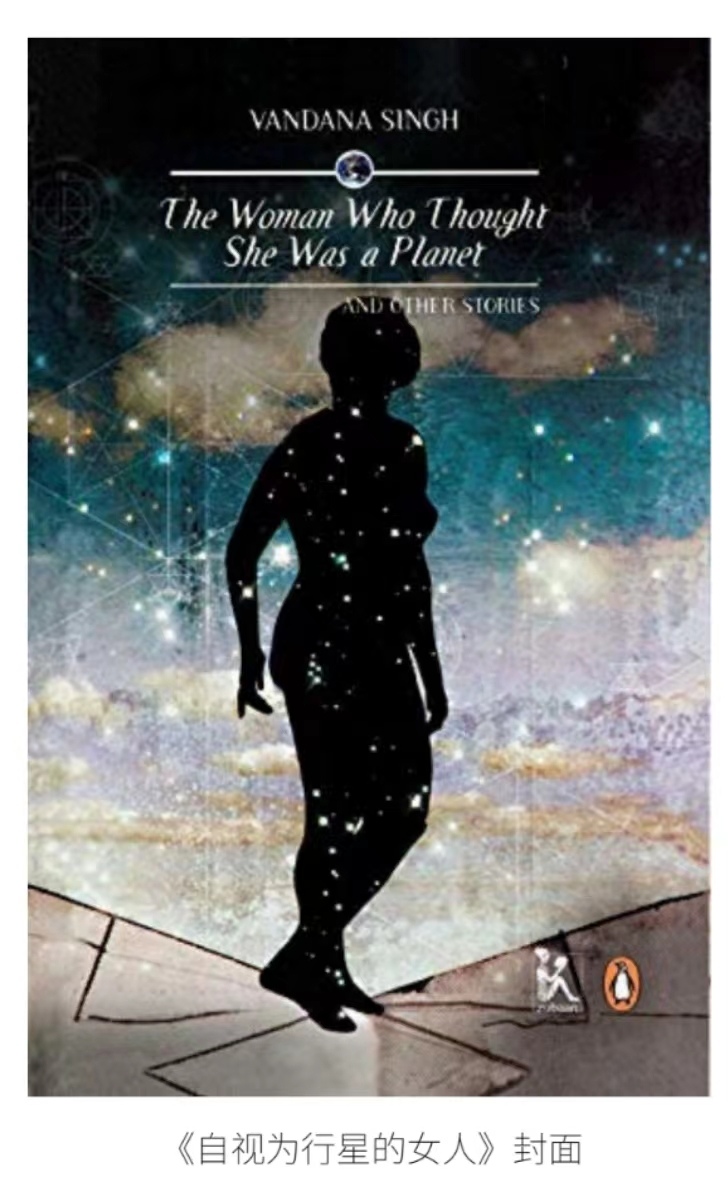
在21世纪初,科幻小说逐渐受到评论界和大众的关注,推想小说创作也不断发展壮大。科幻小说与推想小说已成为呼吁提升道德和关注时事政治的重要阵地,作家们甚至也会借此尝试新的写作风格,试验新的叙事形式。在利米·查特基(Rimi Chatterjee)的《红色信号》(Signal Red,2005)中,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渗透各个科研机构。这一作品既是一部科幻惊悚小说,也是对科学社会学的一次推演。
普里亚·萨鲁卡·查布里亚(Priya Sarukkai Chabria)的《第14代》(Generation 14,2008)在2019年更名为《克隆人》(Clone),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才能成为人类。文章涉及到不同的时间线,交织着历史和未来。休沃恩·乔杜里(Shovon Chowdhury)曾出版两本反乌托邦讽刺小说,即《主管机关》(The Competent Authority,2013)和《孟加拉式特色谋杀》(Murder with Bengali Characteristics,2015),他尖锐地批评了印度的国家专制主义和官僚生活的麻木不仁,展示出一种荒诞的幽默感。萨米特·巴苏(Samit Basu)的作品把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融合起来,吸引了许多忠实读者。他的《被选中的心灵》(Chosen Spirits,2020)将这种吸引力发挥到极致,备受好评。它记录了未来社会的一种“网红”生活方式,在今日媒体泛滥的印度,人们很容易便能找到他们的原型。
在科幻和奇幻杂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其中英德普拉米特·达斯(Indrapramit Das)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他于2015年发表了《吞噬者》(The Devourers),标记着他对自身的突破。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个狼人,作者从孟加拉的狼人神话故事和历史中汲取了多元元素和相关知识。达斯的赛博朋克故事《卡莉娜》(Kali Na)是对神话的批判性追问,同时对社交媒体领域的趋势和危险保持敏锐的认识。苏卡亚·达塔(Sukanya Datta)是一位经过系统训练的科学家,她的多本科幻小说选集以青年读者为目标读者,点燃了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安尼克特·贾维尔(Aniket Jaaware)的连载推想故事选《暗水下的霓虹灯鱼》(Neon Fish in Dark Water,2007)以2050年的虚拟现实为背景,揭示了大城市社会结构的阴暗面。这是一次卓越的尝试,揭示了居住在城市阴影下的被剥夺者与边缘人群的脆弱。
随着人们不断探索科幻小说的比喻和隐喻,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科幻奇幻派作家在创作时迸发出颇有创意的火花。由S·B·迪维娅(S. B. Divya)出版的重要科幻小说选集——《大灾难和其他可能情况下的应急计划》(Contingency Plans for the Apocalypse and Other Possible Situations,2019)收录了她的《小型生物群与大众:一则爱情故事》(Microbiota and the Masses: A Love Story)。故事里,一些患有罕见疾病的人被封闭在具有保护功能的生物气泡内。在那样的身体状况下,走进爱情令人担忧。他们的孤独也引起了作者自身的共情。萨米·艾哈迈德·坎(Sami Ahmad Khan)的《德里外星人》(Aliensin Delhi,2016)通过寓言式叙事,讨论了无处不在的通讯技术——这些技术甚至可能被用作外星人入侵的平台,并让我们重新思考“异化”这一概念。米米·蒙达尔(Mimi Mondal)是一位达利特(Dalit)4作家。她对获得过星云奖提名的美国科幻作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望。同时,她在不少有声望的期刊和杂志上都发表了科幻奇幻故事,包括动人心弦的《在夜晚歌唱的大海》(The Sea Sings at Night,2019),描写了海洋生物与陆地生物之间逐渐模糊的界限。吉蒂·钱德拉(Giti Chandra)也曾创作过奇幻和科幻小说,她的故事《女神项目》(The Goddess Project,2019)体现出她特有的女性主义视野,故事里那些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的居民也颠覆了现存的父权等级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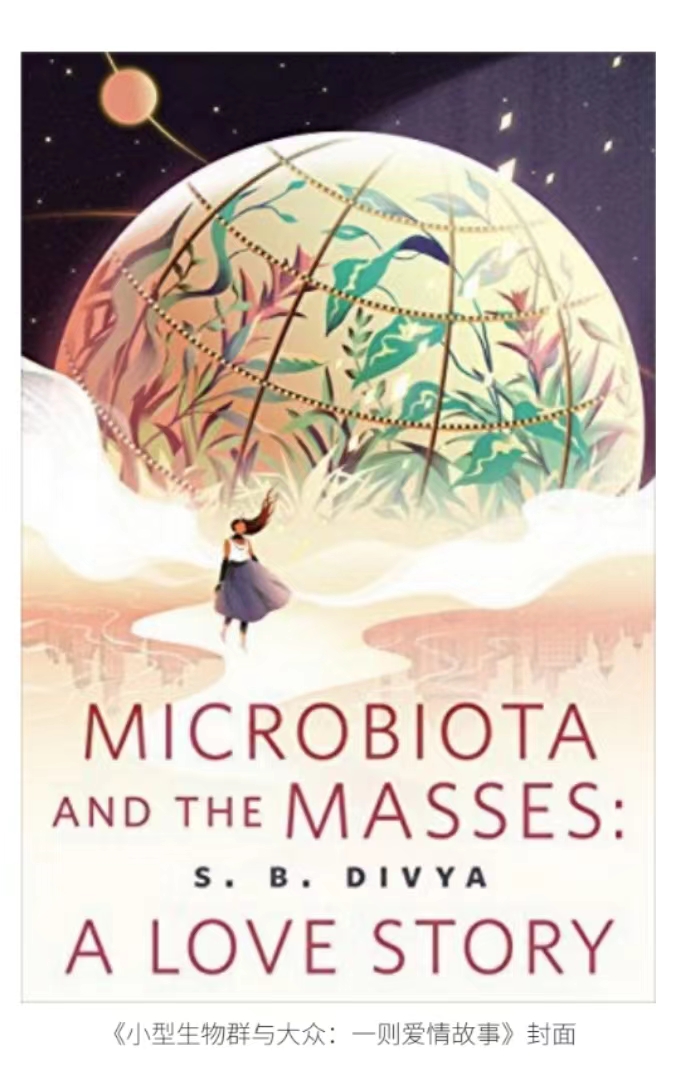
M·G·瓦桑吉(M. G. Vassanji)因离散族裔的文学描写而知名,其创作主题主要包括东非和加拿大的印度侨民生活。在其小说《乡愁》(Nostalgia,2016)中,人们的记忆会在不同的身体间流转,因此在人死后,生命可以得到无限延续。作为小说主角的那位思乡医生发现,若想将“记忆泄露综合症”患者的记忆转移到他人身上,这一过程十分复杂。在这部节奏明快的科幻惊悚小说中,还穿插着对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哲学反思,令读者欲罢不能。与之相似的是,普拉亚格·阿克巴尔(Prayaag Akbar)在《利拉》(Leila,2017)一书中同样描绘了某种反乌托邦的场景,未来社会被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宗教独裁主义者所统治。2019年,这部小说被改编为一部备受关注的奈飞(Netflix)剧集,负责改编的人有迪帕·梅赫塔(Deepa Mehta)、尚克尔·拉曼(Shanker Raman)和帕万·库马尔(Pawan Kumar)。定居班加罗尔的拉瓦尼亚·拉克什米纳拉扬(Lavanya Lakshminarayana)是一名游戏设计师,在《模拟人还是虚拟精英:模拟你的未来》(Analog/Virtual and Other Simulations of Your Future,2020)中,她在同一世界观设定下,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数字化趋势。在故事中,人们所属的阶层和等级,决定着他们能否进入这个数字化的、强大的顶点城市(Apex City)5。这座城市是封闭的,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贝尔公司(the Bell Corporation)的直接掌控。不过即使身处这个处处充斥着模拟化的社会,无论是被标记为“模拟人”(Analogs)还是“虚拟精英”(Virtuals),人们还是能够进行反抗的。于是,在革命中,这一数字技术催生的幻想最终破灭。
另一方面,塔山·梅塔(Tashan Mehta)的作品《骗子的织法》(The Liar’s Weave,2017)建构在架空的历史背景之上,重新讲述了社会边缘群体的历史。在那个世界里,占星术具有真实意义,未来不仅能够被预测还能被改变。主角是来自帕西殖民地的扎汗·莫森(Zahan Merchant),他发现自己的“谎言”可以改变现实、修改时间线并且构建与历史平行的另一世界。那些居住在城市腹地维德罗哈的流浪者希望扎汗可以利用这一特异功能,给他们的世界带来戏剧性的变化。高塔姆·巴蒂亚(Gautam Bhatia)是一名最高法院的律师,同时也是美国科幻杂志《奇异视野》(Strange Horizons)的编辑。在他最近的作品《墙:成为苏美尔编年史的第一部分》(The Wall: Be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Chronicles of Sumer,2020)中,主人公米提拉(Mithila)是苏美尔城的公民。苏美尔城被一道围墙包围着,人们的行动受到这座墙的限制,所有人都遵循着代代相传的规则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而这部小说却质疑了“边界”的合法性,挑战了这一边界在现实和形而上学上的意义。同时,巴蒂亚利用他对法律的敏锐性,在书中描绘了人们如何抵抗限制自由的社会戒律。
与此同时,印度科幻与奇幻创作在网络上也非常活跃。2015年,萨利克·沙阿(Salik Shah)创办了网络刊物《米提拉评论》(Mithila Review),并成为其执行主编。他介绍了不少来自科幻奇幻领域内颇具潜力的作者,刊载了一些推想诗歌、采访和书评。同时,在这一科幻热潮中,许多小说选集也得以出版,由苏卡亚·文卡特拉加万(Sukanya Venkatraghavan)编辑的《魔力女人》(Magical Women,2019)收录了近年来科幻奇幻领域的女性作家作品。根据印度传统的神话叙事,这些故事中的女性角色都被赋予了各种魔法能力,冲击了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信仰体系。S.V.苏嘉塔(S. V. Sujatha)和塔山·梅塔的故事在这个选集里脱颖而出,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维纳亚克·瓦玛(Vinayak Varma)的《奇怪的世界!奇怪的时代!》(Strange Worlds! Strange Times!,2018),是一本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科幻小说选集,收录了斯里纳特·佩鲁尔(Srinath Perur)、英德普拉米特·达斯(Indrapramit Das)以及范达娜·辛格精雕细琢的作品。我负责编辑的《格兰茨南亚科幻小说选》在2019年出版,其第二卷也在2021年面世。这两卷当中的许多故事和诗歌,都来自前文介绍过的才华横溢的印度科幻作家。
此外,在影视界,2001年的电影《德汉姆》(Deham)由戈温德·尼哈拉尼(Govind Nihalani)执导,改编自剧作家曼余拉·帕德马纳班的《器官采买》。电影中,来自不发达国家的捐献者献出自己的器官,移植到发达国家的接收者身上。虽然这个故事在观众当中引起广泛共鸣,但上座率却并不高,没能实现高票房。像这样的尝试还有许多,尽管都是相关电影领域中优秀的导演,不过由于故事涉及的题材过于敏感,电影的市场接受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这种将科幻与其他社会议题相结合的跨界手法,虽然立意很高,但最终还是无疾而终。在宝莱坞,科幻主题常常披着庸俗喜剧或惊悚片的外衣,拉吉库马尔·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导演的电影《我的个神啊》(PK,2014)将其提升到讽刺性喜剧的水平。电影讲述了一名外星人来到地球,对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顽疾感到困惑——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印度社会的问题。OTT服务6平台的到来为更复杂的科幻电影叙事打开了新的大门。导演阿拉蒂·卡达夫(Arati Kadav)2019年的电影《货运》(Cargo)结合了神话和科幻的元素。在电影里,那个世界居住着罗刹人(rakshasas),他们是传说中恶魔的后代,在外太空帮助已故的恶魔重生。

尽管印度科幻目前的发展尚不及英美与中国那样成熟,不过我们在21世纪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有目共睹。科幻的基础是形式上与内容上的实验性,而许多科幻创作的灵感却来自传统的叙事母题,比如神话、史诗、寓言、恐怖与奇幻。这些内容与新时代的科幻元素相结合,迸发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为解决印巴分治与后殖民时代印度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灵感。
虽然经典科幻主题和类型——例如阿西莫夫式的“黄金时代”科幻小说以及后来的赛博朋克,对印度科幻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过当代印度科幻小说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在印度经济与国际社会取得更紧密的联系之后,在多种媒体形式,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出现之后,印度科幻的“自力更生”并不显得意外。
印度科幻小说既涉及不断消解的文化身份,也关注了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并且将当今社会描绘为充满危机的反乌托邦。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生物技术,大型企业的力量在数字时代不断集中,虚拟和仿真技术日益复杂,人们的社交距离越来越远。通过这种“新现实主义”,我们得以想象21世纪印度新的生态坏境与经济构想,以虚构的形式,在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结构中,探索解决矛盾、缓和冲突的方式。实际上,在科幻题材中,古代与现代相互交融,土地与太空相互连结,共同形成某种创造性“异托邦”(heterotopia)7,我们才得以建构或然性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向未来进发。
译者:黄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中国现当代小说外译。
注释
1 “离散”(Diaspora)原指流落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来历经了语义拓展和内涵重构的流变过程,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西方学界用以指代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
2 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文化、反体制行为,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在西方世界大规模传播。伦敦、纽约和旧金山是早期反文化活动的温床。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演进,反文化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随着美国政府对越南军事干预的扩大而演变为一场革命性的运动。
3 “多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带有印度特色,强调占印度人口总数多的主体民族或群体对少数/弱势群体的优越性和可支配性。
4 达利特人(Dalit),汉语中常意译为贱民,是印度和尼泊尔种姓制度的最低阶层。
5 在原著中,“顶点城市”即未来的班加罗尔,在此地,技术是生存的关键,生产力决定力量强弱,人们必须为生活中唯一崇高的目标—成功而奋斗。原文:“Welcome to Apex City. Here, technologyis the key to survival, productivity is power, and the self must be engineered for the only noble goal in life: success.”
6 OTT服务(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又称“过顶服务”或“过顶内容服务”,通常是指内容或服务建构在基础电信服务之上从而不需要网络运营商额外支持的服务。
7 “异托邦”是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阐述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某些文化、制度和话语空间,这些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者”的:令人不安的、强烈的、不相容的、矛盾的或变化的。异托邦是世界中的世界,反映并颠覆了外面的世界。
(排版:张馨木 编辑:齐钰 审定:邹贞)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