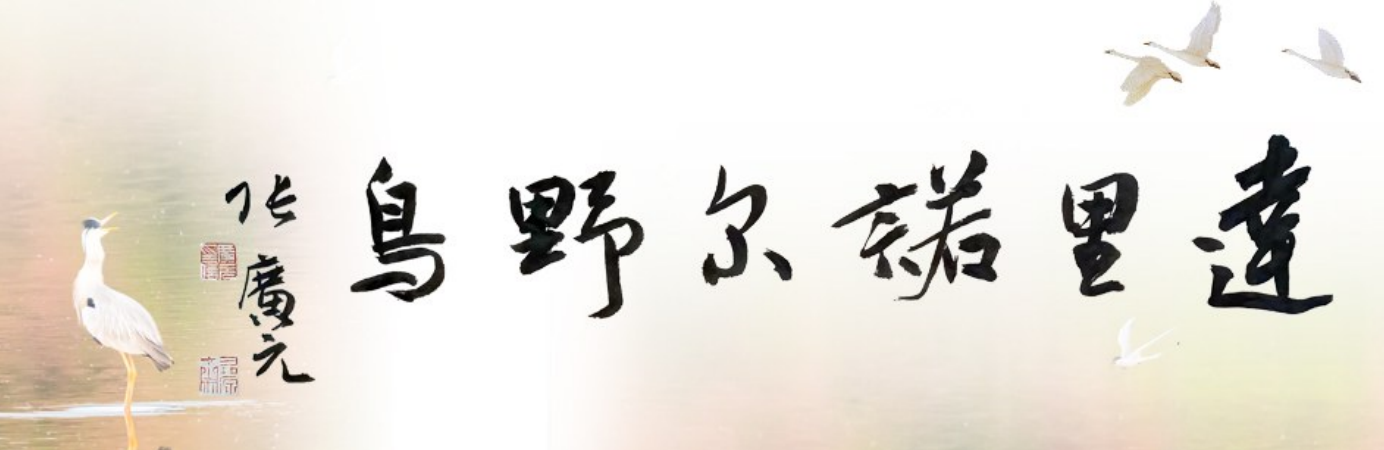
乌力吉牧场位于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里湖南岸,东接贡格尔草原,西连白音锡勒火山群,北临浑善达克沙地,约有二千多公顷。贡格尔草原属于干旱的草原,浑善达克沙地属于半荒漠化沙地草原,白音锡勒火山群有火山爆发时遗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坑,达里湖南岸的乌力吉牧场内有河流、湖泊、湿地、沙地,这种典型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草原大鸟大鸨的栖息和繁殖。
保护区将乌力吉牧场划定为大鸨栖息地加以保护。
大鸨,草原上的大鸟,是一种极度濒危的鸟,被列入《华盛顿公约》cites附录2濒危物种、《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稀有物种、《世界自然联盟》2012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它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全国分布不足千只,世界不足万只,东欧和非洲已经灭绝,英国早在1838年就已经绝种,可见大鸨的珍稀程度,它的濒危程度不亚于国宝大熊猫。
我们看到“大鸨”这两个字,总会想到“老鸨”,这使大鸨这个鸟名很尴尬。
古人认为,大鸨是单性鸟,只有雌鸟没有雄鸟,是“万鸟之妻”的淫鸟,可以和任何品种的雄鸟交配,明代朱权在《丹丘先生曲论》写道:“妓女之老者曰鸨,鸨似雁而大,无后趾,虎纹。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世呼独豹者是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纯雌无雄,与他鸟合。”现代文学家聂绀路在《论鸨母》中说“鸨,淫鸟,借指妓女。”《六书正伪》解释,“鸨”的左字旁,一个“匕”字,一个“十”字,“匕”是雌性生殖器的符号,“十”字是雄性的符号,“匕”和“十”叠加就是交配的意思。
于是就有了老鸨的“鸨”源自一种叫“大鸨”的淫鸟传说,这应该是鸟类最大的“窦娥冤”了。
从上面的解释看,古人对大鸨似乎有些不敬,但西班牙对大鸨相当崇拜,把它当做国鸟。
在乌力吉牧场,我们观察到大鸨平时都是雌雄分群生活的,同性别、同年龄的个体凑在一起形成一个群,即便是在同一个群体,雌性和雄性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只在繁殖季节才短暂地生活在一起,雌性产卵后,卵和幼鸟都由雌性独立照顾,而雄性大鸨早已离开雌性大鸨,与其它同龄的大鸨去游山玩水了。
如此看来,草原大鸟大鸨不仅不“淫”,还相当“保守”。
那么大鸨这个“鸨”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古人造字,一会意,二象形,大鸨的“鸨”字其实就是一个会意字,古人发现大鸨这种鸟都是成群地生活在一起,每群大约有七十只左右,于是给这种鸟造字时把”七十”的“七”和“十”叠加起来,这种鸟的生活习性就表现出来了,因为它是一种“鸟”,就在叠加的“七十”后加一个鸟字,又因为这种鸟较大,就叫“大鸨”啦。
四月下旬,大鸨已经迁徙到乌力吉牧场。
为了近距离观察大鸨的生活习性,我们在大鸨没有到来时,便在大鸨往年经常栖息的地区伪装了一个牧场草垛,人可以藏在草垛里,对大鸨进行近距离观察。
大鸨来了,我们很幸运,一群雄性大鸨就栖息在我们伪装的草垛边,我们可以零距离欣赏大鸨“仙风道骨”般的不凡气度。
我们不急不躁地欣赏着美丽的大鸨,见大鸨的头顶及前胸羽毛都是灰色,上体呈淡棕色,并有密布斑驳的黑色斑纹,下体近白色,足具三趾,眼白色,颊及耳面也呈淡灰色,后颈部为绣栗色,背部为黑色,也有棕色和棕白色的,背部无论呈什么颜色,都排列有序,但宽窄不一,大鸨的腰和尾,羽毛色彩也是棕色但斑色较深,最奇特的是下颌,两侧生有细长而突出的白色羽蔟,像人的胡须。
成年大鸨体长可超过一米,重达十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
它不像鹭类依赖于湿地、干旱草原、疏林草地。半荒漠沙地是它主要的栖息地。
它不像鹤类,没有长脖子长嘴,脖子较粗,嘴也短,身体也没有鹤那么轻盈,显得有些臃肿华贵。
它身体强壮,有一双粗壮的长腿,跑起来“昂首挺胸”的样子,走起路来又似乎有些“呆头呆脑”。
它有非洲鸵鸟之称,但比非洲鸵鸟多一个脚趾,它虽然没有非洲鸵鸟大,但它会飞行,通过飞行可以迁徙几千里。
它是鸟,虽然能飞行迁徙,但更善长奔跑,比草原的骏马、狐狸跑的还快,奔跑时抬头挺胸,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
无论是双脚站立或趴在地面上、窝里,大鸨总是伸着脖子四下张望,警觉地观察周围是否有威胁。
我们长时间观察得知,大鸨的食物很杂,主要吃草原植物的嫩叶、嫩芽、嫩草、种子以及昆虫、蛙等动物性食物,特别喜欢吃象鼻虫、油菜金花虫、蝗虫等草原农田害虫,有时它也在附近农田中取食散落在地的谷粒、玉米粒等。
资料显示,在新的鸟类分类系统中,鸨类已独立为鸨形目,我国仅有3种,除大鸨外,小鸨和波斑鸨分布于新疆,因此我们通常说的大鸨都是指东方亚种(或者叫普通亚种),繁殖于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地;越冬于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江西、湖北等省,偶尔也见于福建。
四月中旬,乌力吉牧场的冬雪已经融化,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雄性大鸨群有些骚动,大鸨们不安地来回奔跑,并发出“丝丝”的声音,仔细观察,有雌性大鸨来到雄性大鸨领地,原来这些所谓的骚动,是雄性大鸨欢迎雌性大鸨的仪式。
于是我们欣赏到了大鸨求偶的整个过程。
一群雄性大鸨,一群雌性大鸨,在我们眼皮底下面对面拉开爱的帷幕,我们观察,大鸨求偶主动方是雄性,雄性大鸨主动出击,在雌性大鸨面前炫耀自己,表达感情。
雄性大鸨们先发出“丝丝”的强烈叫声,然后选择好自己认定的一只雌性大鸨,不紧不慢地跑到它面前,迅速地双腿下屈,慢慢地把脖子伸的直直的,嘴撅的高高的,尾羽向上高高地翘起,并向背部折叠一点一点地收缩,从而露出白色的尾下羽翼,这一点,颇有欧洲骑士的风范。这时的雄性大鸨因为激动全身开始收缩,白色的羽毛收缩成一团一团的,似盛开的白色花朵,一朵一朵的又蔟在一起,然后雄性大鸨开始在雌性大鸨面前跳起舞来,此时雄性大鸨的咽喉部急速膨胀,形成悬挂的气囊,气囊呈蓝灰色,分别挂在颈部两侧,它在雌性大鸨面前走几步,迅速地把头高高扬起,然后向后伸缩,几乎挨到了背部,颈下到眼部的羽毛也竖立起来,尾羽向背部平展呈扇形打开,高高地翘起,几乎与弯曲到背部的头相接,翅膀完全打开了,双翅几乎接触到地面,雄性大鸨围着雌性大鸨一圈一圈地转着,竭尽全力地炫耀着自己的美丽。几分钟后,被雄性大鸨舞姿迷惑的雌性大鸨开始积极主动地去啄雄性大鸨白色的羽毛,然后激情澎湃地亲吻起来。此时的雄性大鸨更加夸张地扭动着身体,尽情地舞蹈,并发出愉快的叫声。听到叫声的雌性大鸨也立刻兴奋起来,它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头快速地伸缩,叫着、转着,与雄性大鸨共舞。
此时此刻,大鸨们正在举行家族生命的延续仪式。
仪式后,雄性大鸨有些筋疲力尽地从雌性大鸨背上跳下来,雌性大鸨也跳到一边,它们煽动着翅膀,抖动着身子,互相瞅了几下,然后各自整理羽毛,没有拥抱,没有告别仪式,就悄悄地分开了。
观察了几天,发现雌性大鸨和雄性大鸨对待爱情的态度并不一样,雌性大鸨受到爱的洗礼后,不会再出现在雄性大鸨群中,而雄性大鸨对爱情就没有那么专一了,有的雄性大鸨每天都会出现在雌性大鸨群前,用它们的雄姿去吸引更多的雌性大鸨,看来,大鸨家族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
雌性大鸨在挑选伴侣时,不仅关注雄性大鸨的舞姿,还会观察雄性大鸨的屁股,看对方的屁股干不干净。
这种现象是有科学依据的。
2014年,西班牙科学家胡安研究发现,大鸨在繁殖前,会大量捕食两种箐科甲虫,这种甲虫体内含有大量的毒素,当它受到攻击时,会分泌这些毒素,从而保护自己。大鸨们经过长时间的进化,生理本能上知道在求偶交配时容易被对方感染,正是出于这种本能的进化,雄性大鸨会在繁殖季节急切地寻找有毒素的甲虫来吃,以便杀死自己体内的病原体,让自己的排泄器官更干净,更整洁,让雌性大鸨看到自己更健康,更强壮,而雌性大鸨出于保护自己健康的本能,在选择配偶时不仅要看对方的长相,还要看对方是否健康。
喧嚣的舞姿十几天后就消失了,乌力吉牧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仿佛一夜之间,大鸨们全部销声匿迹了。
我们知道它们没有走,只是隐藏在茫茫的贡格尔草原、浑善达克沙地、达里湖周边、起伏跌宕的白音锡勒火山群中,雌性大鸨孕育它们爱情的结晶,陪伴生命成长,而雄性大鸨则养精蓄锐,享受交配期后漫长的假期。
七月的乌力吉牧场水肥草茂,是草原最美的季节。一天,我们去乌力吉牧场大鸨栖息地巡护,意外碰到一只雌性大鸨在孵育一窝鸟蛋。那天我们一行三人,驱车沿着达里湖南岸西下,到了白音锡勒火山群下,因为车行受阻,我们只好徒步而行,我们顺着火山群山脉巡护,来到一座火山群山顶,见凸凹不平的火山山顶总体还算平坦,有大量的大小火山石和火山坑。我们走着走着,突然,一只大鸟从我们脚下噗腾着翅膀大叫着跑了出来,它的跑姿和叫声,好像是告诉我们它受了伤,但它并不跑远,却在我们面前不停地重复最初的跑姿。我们仔细观察,原来那是一只雌性大鸨,它的表演让我们知道了它的巢穴就在附近,因为这种表演就是雌性大鸨吸引注意力,保护巢穴的本能。果然,一窝鸟蛋出现在我们面前,山顶草地上的一处火山石中,有一个天然的凹坑,没有任何内垫物,大鸨蛋就静静地躺在这个土坑里,有四枚,蛋有的呈青灰色,有的呈土黄色,上面有褐色的斑点。碰到一窝有四枚蛋的大鸨巢穴太不容易,一般大鸨每窝只产蛋两到三枚,四枚是极少见的。我们知道大鸨的习性,它非常敏感而机警,如果它认为自己不安全了,它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巢穴和孩子。于是我们改道而行,并默默地祝福大鸨母子。
大鸨们享受爱情后,雌性大鸨会独立地去生儿育女,雄性大鸨不需要承担做父亲的责任。雌性大鸨会努力地把蛋生出来,再尽心尽力地用身体进行孵化,大约25——28天后,一只小小的大鸨诞生了,出生后的小大鸨们跟着妈妈学走步、学觅食、学奔跑、学飞翔,到了10月中旬,小大鸨们已经渐渐地长大,跟着妈妈去找其它大鸨的妈妈,这些一同迁徙而来的大鸨妈妈们带着它们的孩子,集聚在一起,长大后再雌雄分群,迁徙到它们冬天该去的地方。
而那些当父亲的雄大鸨们,从不管自己的妻子儿女,或早早地飞走了,或结成一小群,在当地寻找相对比较温暖,农田里有遗落的玉米、大豆、谷类食物的地方过冬了。
冬去春来,这些生活在草原上比大熊猫还珍贵的大鸨们,就这样一年年一代代地生活着。

大鸨 摄影 张新伟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