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世无意识,人类有意识
2016年夏天,美国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以下简称SFRA)年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顺利举行,这也是SFRA年会自2002年之后再次来到英国,而当年度SFRA“朝圣者”终身成就奖(Pilgrim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也颁发给了一位英国学者——西英格兰大学电影与文学教授马克·博尔德(Mark Bould)。博尔德在获奖感言中坦言,对于自己获奖,他倍感荣幸,但也颇感意外,觉得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还没能匹配“朝圣者”奖应有的分量[1]。
但在某种程度上,博尔德的“朝圣者”奖获奖感言是科幻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演讲之一,在2016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上,博尔德作为左翼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外包经济(outsourcing)对于不稳定劳动者(precariat)的压迫和剥削,强调了新自由主义对英国高等教育日益深入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当下的每个人都身陷囹圄,困顿于某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带来的幻象之中,因此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也变得比想象世界末日更加困难[2]。但困难必须被克服,幻象必须被打破,毕竟只有在想象、建构或然性和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实现布洛赫笔下的希望乌托邦,才能塑造后资本主义的时代愿景。由此,博尔德进一步讲道:
在科幻与奇幻领域,我们知道其他可能的世界。
同样,我们也知道,其中某些世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在这些世界中,气候与环境脱离于人类自以为是的掌控,食不果腹、掣襟露肘的贫困阶层竟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价值攫取首当其冲的目标,换上新装的帝国主义继续统治着整个世界,而逐渐抬头的右翼民粹主义、厌女主义、恐同主义以及种族主义日益压缩着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需要竭尽所能,用我们的想象、艺术和学术成果,在社区,在学校,在街头巷尾,通过各种必要手段,来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1]
这些思考,便是博尔德2021年新书《人类世无意识:气候、灾难与文化》(The Anthropocene Unconscious*:Climate**,Catastrophe**,Culture*)的缘起,该部作品也于2022年2月入选了英国科幻协会奖(British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Award)最佳非虚构作品的候选短名单。在这本书的开篇,博尔德邀请读者继续想象种种或然世界,想象温室气体带来的气候变化,想象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洪水,想象淡水资源短缺带来的战争和冲突,想象一个被死亡和恐惧所笼罩的末世废土,想象一个失去所有希望的生态荒原。不过博尔德也提醒我们,这里的希望指的是人类的希望,末世也指的是人类的末世,毕竟人类只是地球的过客。“死亡降临,人类消逝,星球永存。”[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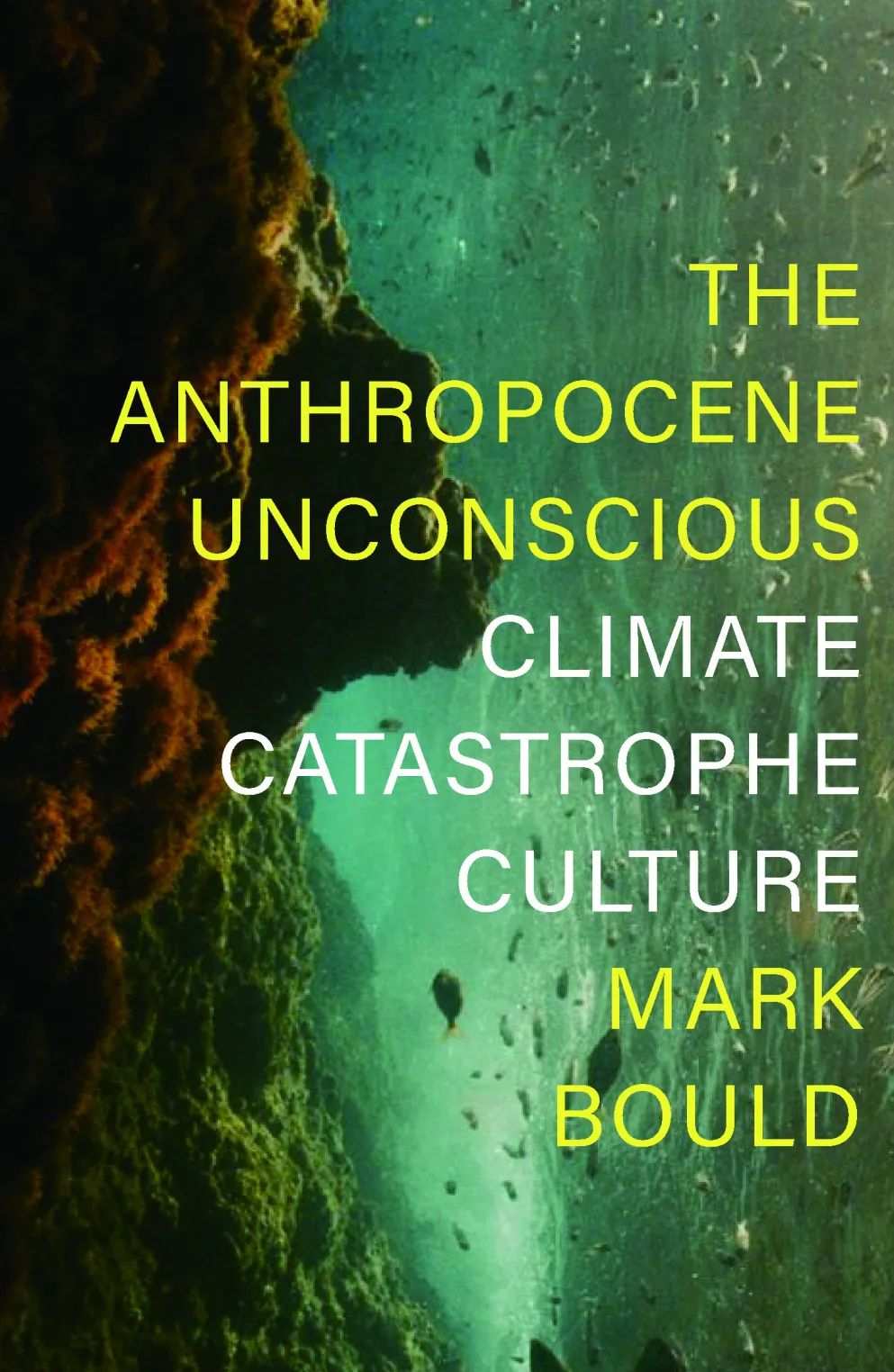
《人类世无意识:气候、灾难、文化》
(Verso出版社,2021年11月)
但即便我们的星球能够永存,人类活动也早已在地质学层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环境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由此形成了一种地质营力,带领我们走进了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我们很难去追溯究竟是谁首先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据博尔德考证,早在1873年,意大利地质学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便已经讨论过“人类代”(Anthropozoic Era,又译灵生代)这一术语,而在乌克兰科学院创始人、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 韦尔纳斯基(Vladimir Vernadsky) 的推动下,苏联在20 世纪60年代正式将“人类纪”作为地质年代单位,等同于目前通用的“第四纪”。不过,博尔德强调,真正将“人类世”推广开来,并使其取得全球影响力的,是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与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他们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人类活动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已经明显改变了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将人类自身的印记深深地刻进了地球漫长的地质演化史[4]。
当然,人类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至今说法不一。在奈杰尔·克拉克(Nigel Clark)看来,人类世的开端应当上溯到160万年前的直立人,他们学会了驾驭火种,而这也是地球上的生物首次有意识、有目的地释放地质与生态环境中贮藏的碳元素[5]。博尔德将奈杰尔·克拉克的论断与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的经典作品《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相联系,故事中的猿人部落在外星黑石板的指引下学会了制作原始工具,獠牙初露,杀死了前来偷袭的花豹,由采集者变为了狩猎者,暴力和征服的基因也由此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但如此一来,这些工具的制造者也被他们自己的工具所改变,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接受着自然的塑造。当人类学会了用火,成为自己的普罗米修斯,百万年后人类过量消耗化石燃料造成的环境灾难也在此刻成为命中注定[3]10。不过除此之外,关于人类世的开端,博尔德还谈到了其他可能,包括35万年前现代智人的分化[3]28,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3]11,1945年美国进行的“三一”核试验(Trinity nuclear test),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消费资本主义[3]10。
在博尔德看来,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也都是不完善的。若人类世可以用一百种方式来定义,这是不是意味着每种定义都只触及到了人类世的某个特定方面?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世这个概念本身便是模糊、流动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强调“人类世”这一总体概念的时候,却忽略了“人类世无意识”,忽略了被人类世总体性遮蔽的具体冲突?在这众多定义中,接受最为广泛的还是克鲁岑的观点,他将人类世追溯到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对蒸汽机的改良。他从气象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极地冰芯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有了显著的增加,显示出全球层面的气候变化[6]。克鲁岑的判断自然是有说服力的,近年来的一系列科学研究也印证了18世纪以来温室气体在地球大气中的快速积累[7]。但博尔德却认为,如果人类世只是用来概括人类活动在地质和气候领域所造成的结果和现象,那在无形之中,人类世忽略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权力关系。
“人类世”是一个方便的叙事。说它方便,是因为它没有挑战现代性的权力和生产战略关系中所内在的不平等、异化和暴力……生命之网中人类活动的多元性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人性”:一个同质的行动单位。不平等、商品化、帝国主义、父权制、种族冲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8]
人类世无意识,人类却有意识。当我们拆解掉“人类世无意识”所建构的宏大叙事,从而得以探究被人类世掩盖的人类“意识”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用新的术语来描述,概括并解释人类世种种现象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些术语包括盎格鲁世(Anglocene)、资本世(Capitalocene)、公司世(Corporatocene)、经济世(Econocene)等[3]7-8。新的术语代表新的故事,新的故事代表新的视角,而新的视角则能够赋予同一现象新的意义。所有这些曾经被遮蔽的意义,共同揭示了人类世的无意识,让我们明白,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现象从来不是人类世的全部。在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看来,人类观察到的种种自然灾害,比如一场洪水、一次风暴、一波反常的高温天气,都是某个“超物体”(hyper-object)的特定表现方式,它们看似独立,实际上息息相关,而人类世正是这样一种超物体[9]。不过对于由此产生的人类世总体性,博尔德显得颇为审慎。他认为,我们应当关注人类世表象之下复杂而多元的话语体系,着眼于细微之处,摘掉人类世的滤镜,去了解每一片拼图碎片以及不同碎片之间的关联。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些碎片,博尔德分析的案例很接地气——小成本电影《鲨卷风》(Sharknado)系列。这一系列虽然有6部作品,但大致内容不外乎都是龙卷风在海上裹挟起无数鲨鱼,袭击城市,居民死伤惨重,而主人公凭借不讲道理的主角光环,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家人、朋友、城市甚至世界。影片叙事支离破碎,剧情发展莫名其妙,视觉特效粗制滥造,基本设定视物理定律为无物,鲨鱼甚至能飞到太空去咬航天飞机。《鲨卷风》系列中充斥着对经典影视作品的戏仿,但这些只是单纯地为了戏仿而戏仿,是片段和符号的堆砌。博尔德在书中调侃道,《鲨卷风》是詹明信式“拼贴”(Jamesonian pastiche)的集大成者,处处体现着对于历史作品的拙劣模仿[10]。
不过,抛开所有表面上的喧闹,博尔德留意到了这种隐藏在符号拼贴之下的“无意识”。他强调了《鲨卷风》使用的大量库存素材(stockfootage),包括纪录片片段、新闻录像等,再现了现实世界中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以及自然灾害。通常来说,一部合格的影视作品中,库存素材、动画 CG 以及新拍摄的影视素材之间的衔接应当是自然而流畅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鲨卷风》并不是一部合格的作品,库存素材的插入非常突兀,从而悬置了影片的叙事节奏,观众不得不从故事中抽身出来,关注这些库存素材本身。诚然,《鲨卷风》的主要关切是市场和资本,但在博尔德看来,《鲨卷风》在进行资本符号拼贴的同时,在无意识中也流露出人们对人类世的担忧。尽管库存素材记录的过度捕捞、过度砍伐、生物灭绝以及气候难民不是影片的重点,但这些片段由于粗劣的剪辑脱离于影片本身,成为相对独立的叙事结构,显示出人类世某种另类的解读方式。对于这种蕴含在叙事“无意识”中的人类世碎片,博尔德还提供了其他的例子,包括《惊变28天》(28 Days Later)、《环太平洋》(Pacific Rim)以及《丧尸未逝》(The Dead Don*’t Die*)等,并以此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带来的改变早已深深地刻进了人类的潜意识,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当下的艺术创作之中。一个幽灵,人类世的幽灵,正在地球上游荡。
二、****失语中的喧嚣同样是在2016年夏天,就在博尔德荣获SFRA 终身成就奖两个星期之后,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 高希(Amitav Ghosh)出版了他的学术随笔《特大紊乱:气候变化与不可思议》(The Great Derangement*: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从文学、经济和政治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世界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据他观察,虽然气候问题是当下人们热议的焦点,但在主流文学领域,人们好像很少对此进行直接的讨论。气候和人类世似乎变成了非虚构作品以及科幻小说的专利,反映出主流文学的集体性失语,即便有少数主流作家开始关注相关议题,高希仍然认为,主流文学并没有对人类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给予足够的重视[11]124-125。
博尔德并不认可高希的论断,他承认主流文学很少直接回应气候问题与人类世危机,但这不意味着主流文学在相关议题上的“失语”。基于《白鲸记》(Moby-Dick)、《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以及《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等经典作品,博尔德认为, 主流文学通过“向心 ”(centripetal) 叙事,放大了故事中各个角色的道德困境,从而塑造了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bourgeois individualism)。于是,隐藏在文本中有关人类世的叙事片段要么被忽视了,要么太过零碎,很难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讨论。由此出发,博尔德更为详尽地分析了英国作家露西·埃尔曼(Lucy Ellmann)的意识流作品《鸭子,纽伯里波特》(Ducks*,Newburyport*)。这部作品没有完整的句子,只有松散的词汇、短语和分句,而在字里行间中,我们慢慢发现,小说实际上是一位中年女性的自我反思,她曾是一名大学教师,在癌症康复后辞去了工作,回归家庭和厨房,琢磨着自己人生的遗憾以及尚未实现的愿望。
不过,博尔德提醒我们,“尽管《鸭子,纽伯里波特》体现了主流文学的‘内向性’(inwardness),对于人类世危机的暗示依然贯穿其中”[3]43。在主人公的思维碎片里,我们很容易便可以注意到诸多与人类世息息相关的叙事元素,包括攫取主义(extractionism)、化石燃料、碳足迹、消费主义、冰川融化、珊瑚死亡、疫病流行、空气污染、生物灭绝、气候移民等。这些内容埋藏于普通人的意识流中,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无法逃避的部分,虽然很多时候这些部分存在于读者视域之外,但它们潜在的影响不应当被忽视。在所谓主流文学的“失语”之下,是属于人类世无意识的喧嚣。
在《特大紊乱》中,高希特别提到了三位具有强烈人类世意识,却没能将其体现在自身创作中的作家,分别是爱尔兰作家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以及高希自己。但博尔德针锋相对,他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相同案例,反驳了高希的观点。金斯诺斯的《觉醒》(The Wake)设定于 1066年的“诺曼征服”时期,以诺曼底公爵威廉为首的法国封建领主入侵英格兰,野蛮地侵占了英格兰人的土地和财产,破坏了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很多人甚至因此沦为农奴,而威廉也自立为英格兰国王,成为威廉一世(William I),通常被称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故事中,主人公巴克马斯特的妻儿都不幸死于这场战争,出于愤怒和仇恨,他组织起一支武装力量,在英格兰东部的林肯郡地区反抗诺曼侵略者。
在高希看来,虽然金斯诺斯针对气候变化的非虚构评论广受赞誉,而且他也身体力行,参与过许多环境主义社会运动,但截至目前,气候议题仍然未能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11]8。但博尔德却认为,即便是在《觉醒》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类世幽灵的影子。对于巴克马斯特来说,早在征服者威廉到来的数百年之前,古老的英格兰土地便已经裹挟在一次更不为人察觉的“侵略”之中,来自罗马的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不列颠,冲击了督伊德教(Druidry)等当地旧有的泛神宗教体系,永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巴克马斯特感叹道:
基督不是土地的神,不是树木、叶子、池塘和冰雪的神,也不是在夏天里郁郁勃发的绿色生命的神。祂只是人类的神,祂告诉你要对天堂充满敬畏,而脚下的土地并不值得祂多看一眼。祂是一个外来的神,来自一片贫瘠的土地,除了人类之外别无所爱。而正因为这个邪恶的存在,法国人才向我们开战。如果你想要活命,就必须战斗,古老的神明将会和你并肩作战。但如果你缴械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在这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12]
这只是众多例子之一。在《觉醒》中,金斯诺斯有意无意地刻画了诸多人类世意象,包括风暴、洪水、大火、资源战争和难民,以及人类在灾难面前的绝望和冷漠。《觉醒》虽然并不是一部大张旗鼓的气候小说,但博尔德通过文本细读,发掘出了故事背景中暗藏的人类世隐喻。他向高希真诚地发问:“这难道还不能使《觉醒》成为一部关于气候变化的小说吗?”[3]53
与金斯诺斯相似,阿兰达蒂·洛伊同样是一位相对激进的环境主义者,高希告诉我们:“洛伊对气候问题的探讨,都是在非虚构作品中呈现的。”[11]8 不过,博尔德认为这比金斯诺斯更难以令人信服。洛伊的处女作《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一经出版,便立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成为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文本,揭示了父权与种姓体系给个人家庭带来的悲剧[13]。博尔德强调了《微物之神》中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多年之后,当主人公之一瑞海儿重返故乡,她发现一切都变了样子,故乡的河“以一个鬼魅的骷髅的微笑迎接她,没有牙齿,只剩了窟窿”:
在下游,为了获得具有影响力的稻农游说集团的支持票,一个咸水堰坝被建造起来了。阿拉伯海淤水处的咸水会流入这条河流,堰坝调节着咸水的流入。因此现在,他们一年可以收成两次,而不是一次,得到了更多稻米,但牺牲了河流。
……
河流曾经具有唤起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但是现在,它的牙齿被拔去了,它的精神耗尽了,它只是一条将恶臭的垃圾送往大海的迟钝、多泥的绿色带状草地。[14]117
自此,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之下,这条河终于变成了通向死亡和腐烂的墓道,“散发着粪便和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买来的杀虫剂的味道”[14]12。由此一来,《微物之神》不仅仅表现了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更展示了这些污染背后的资本逻辑,以及印度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受到的生态剥削。没有无缘无故的污染,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大型工程,隐藏在这人类世面具之下的,是人对于利益毫无节制的追求。
高希曾经说,虽然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恐怖的自然灾难,也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关于人类世的讨论,但他还是没有找到某种合适的方法,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加以论述。不过在博尔德看来,高希完全不需要有意为之。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但在高希的很多作品中,人类世早已成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其中最典型的,是其代表作“鸦片战争三部曲”(“Ibis” Trilogy),包括《罂粟海》(Sea of Poppies)、《烟笼河》(River of Smoke)以及《烽火劫》(Flood of Fire)。该系列以中、英、印三国人民的多重视角,重现了19世纪中期印度洋地区的文化交流,关注了不同族裔、不同阶级的人物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同命运[15]。博尔德指出,高希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偶然间也触碰到了人类世背后的隐秘驱动力。在《罂粟海》中,自给自足的印度农民一开始满足于种植少量鸦片,“家人生病时可以借此镇痛,或是丰收和婚礼时用以庆祝”,而在空余的土地上,他们会种更重要的食品作物,比如“小麦,木豆和蔬菜”[16]。但当他们卷入英国殖民者强加于印度的全球经济体系,成为英国人的债务人之后,鸦片变为农民唯一的选择。
换句话说,人类世早已到来,只是分布不均。通过对几部主流文学作品的解读,博尔德指出了掩藏在文本之下的人类世无意识,但我们回顾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对自己星球的影响已经成为星球的一部分,而我们当下面对的灾难,也会在潜意识中重塑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他看来,高希太小看文学了,前文提到的所有小说,“都不可否认地涉及了气候变化的元素,它们以复杂、细微,甚至笨拙的方式,建构起了文学对于现实生态灾难的指涉”[3]68。
三、****水与木的力量多年以后,在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My Struggle)第一卷《父亲的葬礼》(A Death in the Family)中,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回忆起了他童年时的幻想:
我小的时候,常想象着海水升起来将树林填满,这样一来那些斜坡和丘陵就成了小岛,人们可以在这些岛屿之间行船和游泳。在孩提期间所有的那些幻想当中最令我神往的是这个:想着一切都在我施了魔法的水下面,想着在现在人走路的地方可以游泳,在候车亭和屋顶上游泳;或者潜入水下从一道门滑进去,漂游上楼梯,进入一个客厅;或者就在树林里穿越,游在斜坡、岩石与老树之间。[17]303-304
在人们有意无意地书写、记载或再现人类世的过程里,“水”就像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萦绕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克瑙斯高的回忆显然并不旨在唤起读者的环境意识,他只是回顾自己的童年,梳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除了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克瑙斯高还想起了他小时候自娱自乐的小游戏。而当刚下过雨,附近还未建好的房子下面的地窖“充满了发着亮光的黑水”的时候,他和朋友便会“坐在两个塑料泡沫箱里航行”[17]304。在克瑙斯高用水做游戏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世”概念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而年幼的克瑙斯高也不太可能已经读过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环境主义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而他依然能够想象一座被淹没的山丘,修建一座迷你堤坝,并坐在某个“由长链芳香烃聚合物构成的大箱子”里[3]70,征服一片小的水域。
如此一来,人们对于水的关切早已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植在每个人,甚至每个孩童的心里。为了探讨“水”的意象在人类世无意识中的意义,博尔德重点分析了两部出版于20世纪中期的科幻作品,即阿瑟·C. 克拉克的《深海牧场》(The Deep Range)和 J. G. 巴拉德的《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在《深海牧场》中,前宇航员瓦尔特·弗兰克林因航天意外患上了恐高症,不得已来到深海牧场工作,人们在这里养殖鲸鱼,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了一系列畜牧产业。在适应了新的生活之后,弗兰克林努力改变了这一产业,他劝说人们不再食用鲸鱼,转而停止杀戮,开始消费鲸的奶制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深海牧场》刻画了一个罕见的海洋乌托邦,人们在小说最后似乎与自然和鲸达成了某种和解,实现互利共赢。不过,博尔德认为,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乌托邦,一个虚假的乌托邦[3]74。虽然故事里人们改变了自己的食谱,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依然屹立不倒,人类的主体性霸权依然存在。隐藏在深海中、一直对牧场虎视眈眈的海怪时刻提醒着弗兰克林,人类的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并由此建构起尚未被资本逻辑所吸纳的外部空间。而这样的外部空间,正是资本扩展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海怪的猎杀,也可以视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与此相比,巴拉德的《淹没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2145年,由于强烈太阳辐射造成的气候变暖,地球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海平面升高,淹没了大部分陆地,沿海地区统统变成热带浅水湖,而全球气候也变得不再宜居。同时,地球上的植物与生物也发生变异,变得硕大无比,某些变异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类理解。作为科幻“新浪潮”(New Wave)的代表作家,巴拉德避开了克拉克作品中体现出的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垂直的等级关系,将二者置于同一水平面之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非人间的界限也因此消解。小说最后,主人公宛如第二个亚当,“跟着潟湖的踪迹,穿过雨水和热气”,走向南方,走向未知,走向融合[18]。
在博尔德看来,自古至今,地球上的江河湖海都在提醒着人类的渺小,我们从未真正地征服过水,即便我们有时能够和水达成暂时的协议,借它的力量开拓新的市场,探索新的能源,但也只有世代生活在水边和船上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种力量的狰狞。在《深海牧场》和《淹没的世界》基础上,博尔德带领读者回顾了四部与水相关的电影,包括《缓缓前行的老货轮》(DeadSlow Ahead)、《三峡好人》、《迷失河流》(Lost River)以及《进化岛》(Évolution*)*,进一步梳理了人类与水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文化终会消逝,但我们留下的印记却会成为整个星球的伤疤,瓦砾、塑料带来了无法消解的污染,石油资本主义(petrocapitalist)制造了难以想象的碳排放,所有这些都打破了人与水之间的协议,释放了后者蕴藏的可怖力量[3]100。
而同样具有力量的,是木。与水不同,木的力量少了一丝波涛汹涌,多了一点盘根错节。在沃伦·埃利斯(Warren Ellis)与杰森·霍华德(Jason Howard)合作的漫画作品《天外来树》(Trees)系列中,来自太空的树状生命体降临地球,它们巨大无比、高不可攀,成为某种主动与人类接触的“巨大沉默物体”(Big Dumb Object):
异树登陆,已有十年。它们遍布世界,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不语。如入无人之境。犹如足下无物。十年之前我们便已经了解到,宇宙中还有其他智慧生命。可是他们却不视我们为智慧生命,甚至连生命都算不上。它们矗立在地表如同参天巨树,对这个世界只以沉默施压,犹如身在无人之境。[19]
巨树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但在根基附近,有一种罂粟花开得艳丽。这种花的生长不需要土壤,也无所谓阳光,甚至能够产生无线电干扰。通过进一步调查,人们在罂粟花瓣上发现了精密的电子线路,这些属于机器的元素在生物基底上生成、延展。故事中的科学家马什认为,每一朵罂粟都是巨树生命体的一个细胞,而当细胞发展成组织,组织成长为肌体,巨树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一种超强电磁波,将会融化两极冰盖,而由此产生的暖流,也会把罂粟的种子带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博尔德很重视漫画里巨树所蕴含的联结性,他将这种联结性归因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提出的“蜘蛛世”(Chthulucene),体现出关系的流动性与“触手性”(tentacularity)[20]。发源于巨树的罂粟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它们还能与其他生命体进行融合,在人的身体上生长。在博尔德看来,这些巨树和罂粟是来自未来的使者,来自蜘蛛世的使者。它们让人类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时间,消解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线性关系,打破了人类主体针对他者的暴政,将人类卷入了某种生命之网,标志着人类世的终结[3]113。
对于这样以树根和藤蔓为象征的生命之网,博尔德还介绍了许多案例,包括电影《明日边缘》(Edge of Tomorrow)、《降临》(Arrival),甚至还有 DC 漫画中的《沼泽异形》(Swamp Thing)以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丛林人》(The Woodlanders)。不过在博尔德看来,最能体现木的力量的作品,要数美国作家理查德· 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新作《树语》(The Overstory,又译《上层林冠》)。小说以树为主体,分为四个部分——“树根”“树干”“树冠”以及“树种”,并借此影射了一棵参天巨木的生命周期,而小说的叙事也像树一样,充满了分支——网络、对话、隐喻和根系。故事中出现了9个人物,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生活在不同时间,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交集,但他们中没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主角。故事的主角是树,确切地说,是人和树的关系,一种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式相互生成(becoming)的关系[3]126。当然,博尔德眼中的树,并不是德勒兹所批判的二元“树状”(arborescent)结构。他强调的是树的根系以及这些根系在地下构成的大网。他认为,真正意义上属于人类的世代或许从未存在,这是属于树的世界,是属于树状关系的世界,而人类只是这张关系之网上的匆匆过客[21]。
最后,让我们回到博尔德《人类世无意识》的开篇,以及他邀请我们一起想象的“其他可能的世界”。多年以来,甚至自古以来,在这些对于或然性的想象中,人类世的幽灵一直挥之不去,海面上升、沙漠蔓延、极端天气、淡水短缺、全球饥荒等元素在人们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随处可见。博尔德反驳了阿米塔夫·高希的观点,认为即便很多作品并没有将“气候”或“人类世”一词印在封面上,这些概念依然体现在作者的潜意识中,体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中,体现在读者的解读过程中。他指出了“人类世”一词的复杂含义,解释了被人类世叙事所掩盖的其他权力关系,并且通过水与木的意象,质疑了人类世中固守“中心”、奴役他者的人类主体。他想象了一种“后人类世”的或然性,一种攀附于树木枝蔓的或然性,一种实现了无限“生成”的或然性,一种建构于蜘蛛世的或然性,一种属于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眼中“游牧主体”(nomad subject)的或然性[22]。他说,《速度与激情》(Fast and Furious)系列所象征的“大加速”时代(The Great Acceleration)已经落下帷幕,而我们也应当像生态女性主义者沃尔·普朗伍德(Val Plumwood)所呼吁的那样,寻求叙事范式的转变,要承认并接受自然的叙事主体,用更丰富的词汇重新想象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与其他物种、其他心灵建立对话的机遇[23]124。
通信作者: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英科幻文学、乌托邦、政治经济等。
参考文献:
[1] BOULD M. Pilgrim Award Acceptance Speech [J]. SFRA Review,2016(317):11-14.
[2] FISHER M. Capitalist Realism: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Winchester:Zero Books,2009.
[3] BOULD M. The Anthropocene Unconscious [M]. London:Verso,2021.
[4] CRUTZEN P J,STOERMER E F. The Anthropocene [J].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2000(41):17-18.
[5] CLARK N. Rock,Life,Fire:Speculative Geophysics and the Anthropocene [J]. Oxford Literary Review,2013,34(2):259-276.
[6] CRUTZEN P J. The Geology of Mankind [J]. Nature,2002(415):23.
[7] STEFFEN W,SANDERSON A,TYSON P,et al. Global Change and the Earth System:A Planet under Pressure [M]. Berlin:Springer,2004.
[8] MOORE J W.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M]. London:Verso,2015.
[9] MORTON T. Hyperobjects: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3.
[10] JAMESON F.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M]. London:Verso,1991.
[11] GHOSH A. The Great Derangement: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M].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12] KINGSNORTH P. The Wake [M]. London:Unbound,2015.
[13] CHAE Y. Postcolonial Ecofeminism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J].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2015,51(5):519-530.
[14] ROY A.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M]. London:Flamingo,1997.
[15] 郑楠 . 现代印度的三种面向——论“朱鹭号三部曲”中的政治书写 [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1):113-122.
[16] GHOSH A. Sea of Poppies [M]. London:John Murray,2009.
[17] KNAUSGAARD K O. A Death in the Family [M]. Trans. Don Bartlett. London:Vintage,2014.
[18] BALLARD J G. The Drowned World [M]. London:Fourth Estate,2014.
[19] ELLIS W,HOWARD J. Trees,Volume 1:In Shadow [M]. Berkeley:Image Comics,2015.
[20] HARAWAY D J.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M].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
[21] WOHLLEBEN P. The Hidden Life of Trees:What They Fell,How They Communicate-Discoveries from a Secret World [M]. Trans. BILLINGHURST J.London:William Collins,2016.
[22] BRAIDOTTI R. Nomadic Theory:The Portable Rosi Braidotti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23] PLUMWOOD V. Nature in the Active Voice [J].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2009(46):111-127.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