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三部曲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让我们再次关注中国科幻在其他土壤生根发芽的可能性。许多从业者与研究者将《三体》之后引发的中国科幻外译热潮称为“后《三体》时代”,不仅更多作者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韩语等,译者的队伍也日渐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体》在海外获得的空前关注是未有先河也难以复刻的个例,中国科幻在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大环境下并不是一片真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科幻作家是进行文本产出、文体实验的中坚力量,相比前辈从科普出发、在写故事前需要打下坚实科学知识基础的传统,“科”与“文”的界限在新时代科幻作家的笔下愈发模糊了。当下的中国科幻正在三个不同的位面,日拱一卒般冲击着传统与固化印象:类型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区隔、网络媒介与传统印刷纸媒的区隔,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区隔。
纸托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华语文学英译来支持译者的工作,该平台亦是英语世界最大的系统性介绍华语文学的平台之一。笔者曾受邀为2022年初出版的《纸托邦当代华语文学指南》(Paper Republic Guid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撰写“中国科幻”一章,从该书的结构便可得见,中国科幻已经在当代华语文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备受关注的作家不仅有刘慈欣与韩松,还有早已被英语读者熟识的新生代佼佼者陈楸帆、郝景芳、宝树等。可以说,中国科幻英译已然“破圈”,不再被局限在类型文学之中,而是成为了英语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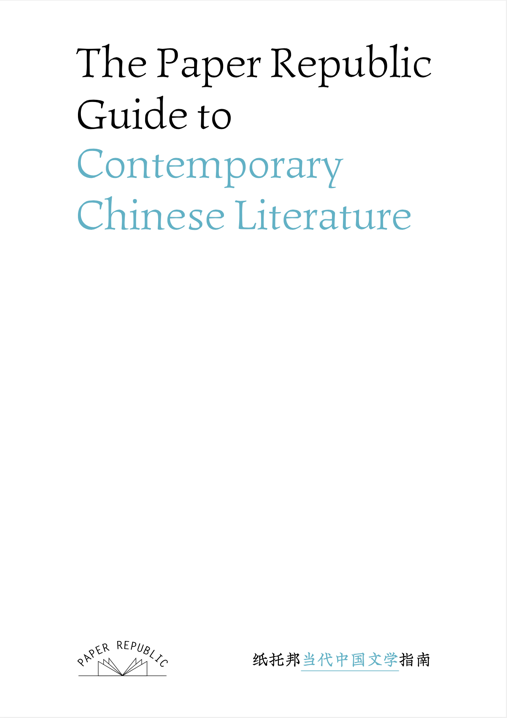
《纸托邦当代华语文学指南》(Paper Republic Guid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图书封面
(图片来自亚马逊)
从更侧重流行娱乐、主要靠网络传播的粉丝文化角度看,网文科幻如一十四洲《小蘑菇》与Priest《残次品》,不仅在近些年得到了诸如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这样关注实体出版物的科幻大奖的认可,也引发了读者自发的英译,在英语世界自行形成了庞大的粉丝群,启发了更多亚文化与同人创作。
那么,这是否标志着中国科幻已经在“后《三体》时代”彻底融入了世界呢?在此我们需要先定义何为“世界”。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研究中十分经典的“中心与边缘”概念表示,英语与英语文学处于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作为“守门人”的话语权[1]。我们在讨论“世界”的时候,大多时候都在默认指涉英语世界——它极大地影响了何种创作题材得以流行、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具有“普世价值”,以及文学市场该遵循怎样的游戏规则等问题。与之相对的边缘语言与文化想要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一个角色,或多或少都需要进行迎合。下文所提到的“世界”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适用。
与“世界”密切相关的则是围绕着中国科幻之“中国性”的种种迷思,以及它和东方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方主义首先是一种权力结构,映射的是殖民者和强势文化与被殖民者、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它可以带着丑化歧视与猎奇赞美的双重面孔出现,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痴迷夸张的啧啧称奇,都是东方主义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将其视作“文化入侵”的洪水猛兽,或是“比我们落后的地方一定没有真正的科技与科幻”这样的贬低,另一方面则当作是满足对“神秘东方古国”的窥视欲与好奇心的渠道。当众多英语读者默认科幻题材源自西方时,市场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科幻的审视便未免带着更深一层的刻薄。当中国科幻凝视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在凝视中国科幻:你是否符合我们心目中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写的科幻”的刻板印象?你要如何证明自己对我们的价值?这样的“证明”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作家或是模仿英语世界标准,严丝合缝地融入创作主流,专门创作高度符合英语文学传统定义中的“科幻”的作品,通过这种与东亚文化割席的方式来摒弃刻板印象的束缚;或是迎合刻板印象,刻意夸大渲染“喜闻乐见”的东方元素来吸引眼球,以证明自己有别于英语科幻的独特价值。此类尝试宛如火中取栗,亦会演变成对东方主义的无意识内化,在一次次践行既有审美与市场标准的过程中,持续将自己的语言与传统排挤至边缘。
《三体》英译的火爆仅仅是迈出了一小步。更深远的问题是,翻译到海外的中国科幻,是否能够被接纳为百花齐放的科幻大家庭的一员,而非“窥见当代中国的一扇窗”?何时任何一位中国科幻作家在加入国际圆桌讨论会时,可以顺畅平等地讨论科技、环境与情感,以创作和思想论短长,而不是被迫单枪匹马地为自己的国家、语言与文化做代言人?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幻想小说的评价即是反映了世界对当代中国的幻想——其中不乏奇想与空想。
在这样的情形下,翻译本身即是与中国科幻研究骨肉相连的话题:译者在中国科幻出海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译者的工作是仅限于文本创作本身,还是延展到了整个的文化交流与出版流程之中?传统印象中的翻译似乎总是更次一级的,存在意义也仅是为了忠实地为原文服务。那么,这个范式能否被颠覆?翻译有没有可能反过来推动文学本身的发展与真正地提升作家的文体自觉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呢?
早在2018—2019年,热衷翻译文学的科幻活动者便展开过一次讨论:随着英译科幻小说越来越多,是否有必要在雨果奖单独设立一项“最佳翻译文学”?在此之前,《三体》是唯一一部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翻译作品。知名美国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的主编尼尔·克拉克(Neil Clarke),也是长期与微像文化合作中国科幻英译专栏的发起人之一,在个人博客里反驳了这个提案。他认为,这样的奖项看似是在为翻译文学增加曝光度,实则却在强化英语的中心地位[2]。诚然,倘若全部译作都要率先被打上“翻译”的标签,那么似乎也是在暗示,只有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小说才当得上文学意义上的“最佳”,得以登堂入室,而其他语言的小说只能在单独为它们辟出来的边角小游乐场自娱自乐。“翻译”二字仿佛在此成了某种地位更低、水平更差的象征。这无疑也呼应了前文所说的,“世界”二字在文化相关的讨论中其实暗含陷阱,那就是它默认“英语的就是世界的”,英语文学与其他语言的文学之间存在一套隐藏的等级制度,文学的好坏标准也自然基于英语世界的经验与口味而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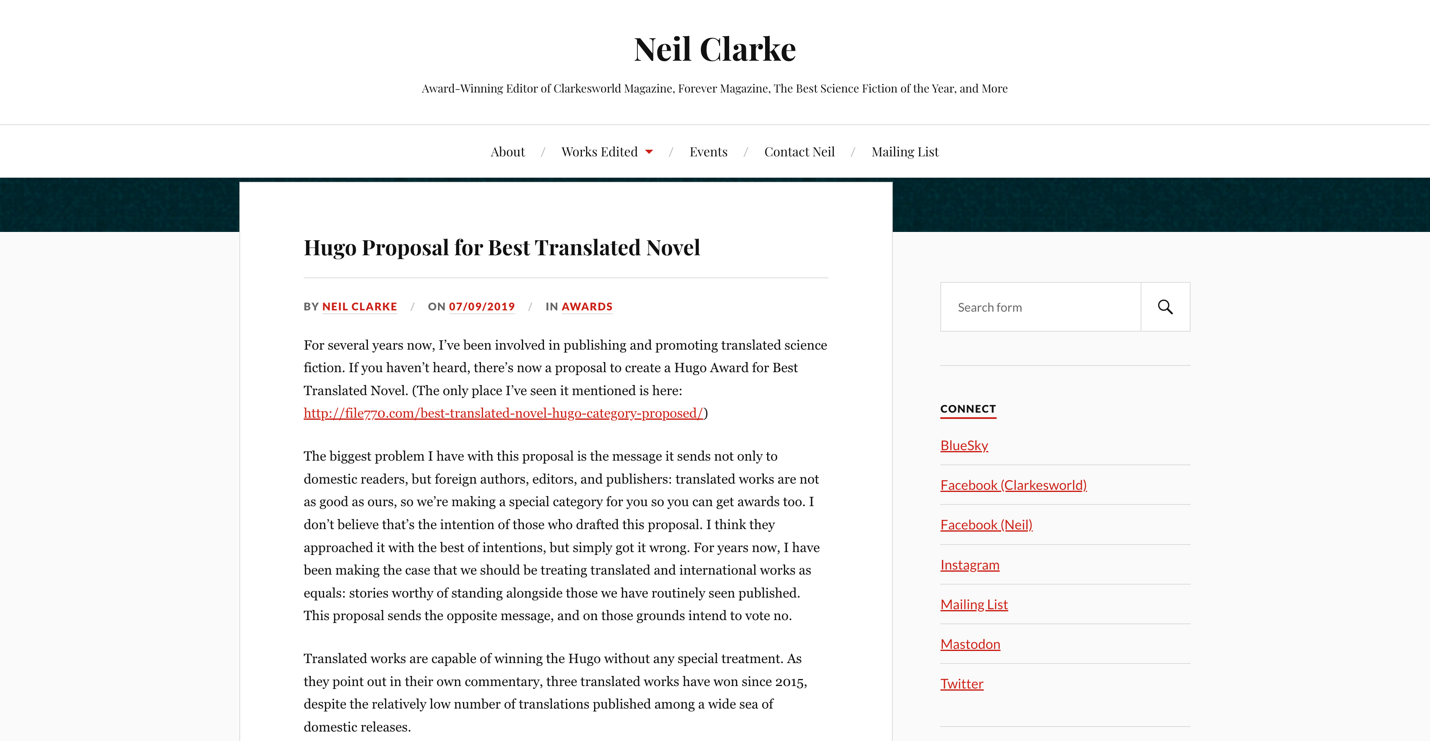
尼尔·克拉克(Neil Clarke)的个人博客页面
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则要更激进一些,那就是直接绕开翻译的制约,让全部语言的作品一起参评。我们为什么要默认雨果奖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呢?2023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已经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尝试,不再偏重照顾英语读者,参会的中国读者纷纷提名自己最爱的华语科幻作品。这一变化可以被视作坚实的声明:世界科幻的核心并不只有一个,所有科幻读者的声音都应被忠实地听到,而不应该被“翻译”自带的壁障稀释与扭曲。这当然也是笔者想要看到的理想未来。然而,正如前文提到,在英语强势的环境之中,中文与华语文学仍然身处边缘,这样的抉择也会导致作者难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读者群,或许只会形成又一个被语言天然分割的、孤立的小游乐场。这样看来,中国与由英语主导的世界之间仍有鸿沟,而想要跨过这道区隔,也并非是一次声明、一些强调文化多元重要性的举措就可以完成的。
这似乎变成了一个难解的困局。正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提出的那样,故意要求一篇译文读上去和目标语言创作的文学别无二致,其实是让译者与原文本所代表的语言与文化隐形,形成一种对原文本与文化的抑制[3]。然而,译者的“显形”在文化权力明显不平等的情况下,似乎同样会遭遇尼尔·克拉克所描述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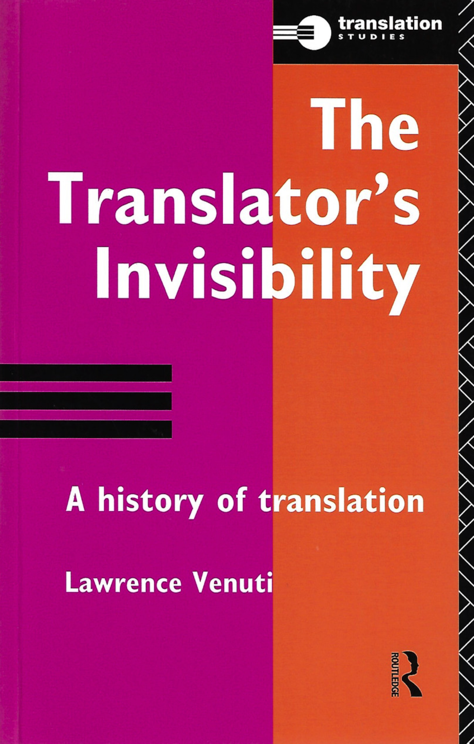
《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图书封面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我们不妨将关注点的焦距拉远一些。翻译是一项工作、一个行为,却也可以是一种媒介。既然如此,“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在这里似乎同等适用。当我们把目光从翻译后的成品转开,转而审视翻译过程本身的时候,便能够发现,先前的讨论还是大多建立在二元的基础上,将“中国与世界”“译文与原文”等概念对立起来,然而翻译所具有的正是超越二元的能力。例如笔者从译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科幻外译给我们的启迪其实是跳脱出以上种种框架的全新选择。笔者近期的两部译作:《春天来临的方式》(The Way Spring Arrives and Other Stories,于晨、王侃瑜、Ruoxi Chen、Lindsey Hall合编)与《AI 2041》(陈楸帆与李开复合著,简体中文版书名为《AI未来进行式》)的英文版。
《春天来临的方式》是第一部全女性与酷儿创作者的中国幻想小说英译合集,从诞生之初即是一场盛大的跨国合作,更是明确了一个重要的目标:以往的中国科幻英译作品将男性作家置于聚光灯下,这本书致力于将关注焦点转向女性与酷儿作者、译者、编辑等同样在成书过程中付出心血的创作者。其中值得称道的是,在敲定多人组成的译者团队之后,编辑并不遵循“先到先得”的惯例,而是加入了筛选与配对的流程,仔细研究每位译者的过往译作、简历与喜爱的风格,为译者找到最适配的作品。不仅如此,书中还收入了多篇非虚构文章,专门由译者来分享心得。在这里,翻译不再是面目模糊、被要求成为迎合目标语言的隐形人,也并未被当作文化猎奇的卖点。跳脱出这样二分法的诀窍正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将传统中被忽略的声音置于聚光灯下有力地表达:翻译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与其囿于“忠实与不忠”,不如采用更广阔且具有批判性的视角,去看待翻译本身。译文的质量与审美自然由读者自己评说,但更重要的是,读者应意识到他们在阅读的就是自成一体的翻译文学,也应借此稍稍窥见译者脑中神秘黑匣的一角,而非抱着对传统华语文学或是英语文学的刻板期待而来。

《春天来临的方式》(The Way Spring Arrives and Other Stories)图书封面
(图片来自亚马逊)
而《AI 2041》更是独一无二的例子,生动地演绎了多人创作模式的可能性。书中包含十篇由陈楸帆创作的科幻小说,每篇小说围绕一种与AI有关的核心科技展开,搭配一篇由李开复撰写的科普介绍文章。小说中涉及的科技与未来想象更是由两位作者与庞大的研究团队一同构建。该书第一版为企鹅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版,陈楸帆用中文写完初稿后,交予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译者翻译成英文,再由英语编辑联合作者、译者一同修改。陈楸帆优先考虑了文本能否被更便捷地翻译,因此选择用更简单的句式结构来呈现故事,以表达清晰和叙事性强为首要目的,而非着力于中文复杂的诗性。可以说,他在行文过程中是根据英文本身与标准英文叙事的结构来为中文草稿建模。以英文的认知逻辑用中文行文,这无疑也在拷问现代汉语本身的弹性——它是否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方式,容纳其他语言、文化与思维方式经由某种形式的“翻译”汇入它的语料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文本的“翻译性”被淡化时,中译英中出现的权力不平等与有关东方主义的种种担忧,也由此得到了一定的消解。或许译者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变得更为隐形,但这样的隐形却主要源自作者与译者这两个传统角色的瓦解,而不是排挤与偏见。《AI 2041》作为一部真正的跨语言、跨文化作品,十个故事横跨十个不同的城市,由一位中国科幻作家写给世界,第一版是英语——这个例子不禁让我们开始思考,是否应该重新界定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的诸多标准:作品的第一语言是什么?是初稿的语言,还是第一版印刷物的语言?如《AI 2041》这样以中文落墨却以译文的句式语法写给世界的作品,它依然还是一部译作吗?

《AI2041》英文版图书封面(图片来自亚马逊)
这样全新的创作模式也反映了一种世界文学的新走向:作者、译者与编辑的角色可以模糊——不再是传统中译英出版线性的范式,即作者把定稿给到译者,译者完稿后再交予编辑,而这位编辑绝大部分情况下对中文是一窍不通的,仅能从英语市场的角度去修改译文;而是让作者、译者与编辑形成一个持续对话的场域,三者互相影响。最重要的是,能够达成这样的创作模式,也和新生代作者本身有极大的关系。笔者提到的两本书中的作者们大多熟练掌握英语,在创作之初便受到国际文化产品的影响,是读着译作长大的一代。作者与译者合作时,得以直接阅读译稿,对英文文本做出评论,与译者探讨时,甚至自己上手用英语直接修改。因此,作者在译文的成型中扮演的角色,与在原稿中几乎同等重要。译者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威性与自由度,不再被看作是无味的滤纸抑或无色的隐身人,译者自身的抉择、审美、风格得以影响甚至塑造英文版的内容和修辞。
译者从幕后走到台前时,翻译与被翻译、原文与译文、中国与世界的二元性也次第瓦解。因此,翻译即是恒久具有波动与不确定性的空间,自身便具有产生新鲜血液的能力。其中,译者既不隐形也不完全可见,而是扮演了共情的媒介以及用另一种语言孕育着故事的子宫。译者不再是孤独闭塞的劳作者,而是与整个出版团队形成共生关系,同脉同息,多方交流,两种语言也自由地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旧的世界文学模型正在逐步被消解,就连“何为创作”的过程都在被重新定义。
在针对权力不平等进行种种合理的抵抗,除推进去中心化之外,我们同时需要做的另一件事,即是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体系,一边与既有的结构和规则进行交涉,一边努力讲自己的故事。我们更应该思考“科幻还能怎么写”。以《春天来临的方式》与《AI 2041》为跳板,倘若现在科幻这一文学类型的中心依然扎根在英语世界,那么中国作家把自己代入“我本位”的思考方式,可以率先尝试让科幻去中心化,让这个题材成为真正兼容并包的题材。而身为译者,抱持着身为“中间物”的自觉性,但在翻译中不再隐形而是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或许也可以在一次次的搭桥中建立起前所未见的语言交流体系,为封闭迟滞的系统撬开一条细缝,让文化更好地流动起来。
相较回答问题,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铺陈一个场景,然后提出问题。走向世界的中国幻想,与世界幻想中的中国,正在以当下蓬勃飞速发展的中国科幻为试验场,迸溅出无数绚丽的新答案。
(本文雏形为笔者于2023年7月在复旦大学多语种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科幻小说翻译与国际传播论坛”进行的发言)
作者:金雪妮(Emily Xueni Jin),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候选人,青年学者,中英、英中译者,作者。评论类作品见《矢量》(Vector)、《纸托邦当代中国文学指南》(Paper Republic Guid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与第六声网站(Sixth Tone)个人专栏等。
参考文献:
[1] CASANOVA, P. What is a Dominant Language? Giacomo Leopardi: Theoretician of Linguistic Inequality [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13, 44(3): 379-99.
[2] CLARKE, N. Hugo Proposal for Best Translated Novel [EB/OL]. (2019-07-09) [2023-10-19]. http://neil-clarke.com/hugo-proposal-for-best-translated-novel.
[3]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