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T News
利维坦按:
前几年看了一部经典影片,中译名《无语问苍天》,实际上原片名为“Awakenings”,译作苏醒、唤醒都可以。
该电影以大名鼎鼎的神经医师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的同名回忆录改编,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对于昏睡性脑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患者使用左旋多巴治疗的实例。
《Awakenings》剧照。片中医生马尔科姆由罗宾·威廉姆斯饰演,饰演患者伦纳德的则是罗伯特·德·尼罗。© 豆瓣电影
左旋多巴的治疗初期效果明显,很多脑炎后遗症患者恢复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患者开始对药物变得极为敏感,行为也逐渐失常。不过,虽然治疗昏睡性脑炎存在极大争议,但左旋多巴至今却仍是治疗帕金森病的首选药物之一。
多巴胺(Dopamine)是大脑中的化学信使,曾经是神经科学界的术语——你可以在生物学教科书中读到它。但如今,多巴胺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专注、渴望和快乐的代名词。
浏览TikTok或晚宴坐在硅谷的软件工程师旁边,你会听到看到各种多巴胺相关的信息。很难放下手机?也许你需要一次多巴胺排毒。担心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试试多巴胺断食,或者为了快速提升情绪,可以试试多巴胺穿搭。
想要破解你的大脑并不是某种小众的事情。著名神经科学家兼播客主持人安德鲁·休伯曼(Andrew Huberman)2021年发布的“多巴胺大师课”中,一集名为“控制你的多巴胺以获得动力、专注和满足”的视频,在YouTube上已获得超过900万次观看——对于一个136分钟的神经科学解释视频来说,这个浏览量属实惊人。该视频以及其他类似的视频,提供了各种控制多巴胺释放的技巧。有些是行为上的,比如戒糖或戒除色情成瘾。还有一些涉及购买补充剂、手机应用程序或生活指导。
但实际上,多巴胺的作用比流行文化赋予它的既多也少。虽然基于多巴胺的健康趋势通常依赖于其作为“快乐分子”的角色,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今天都同意,多巴胺并不直接代表快乐。它在大脑中的作用是广泛而微妙的,影响着从行为动机到生理恶心的一切。在大脑之外,它有助于扩张血管、降低白细胞活性等。甚至植物也会产生多巴胺[1]!
与此同时,多巴胺并不是唯一驱动我们生产力、情绪的因素。硅谷的布道者们声称,如果我们能够破解我们的多巴胺系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这既简化了人类大脑化学的复杂性,也夸大了我们优化意识的能力。
“像安德鲁·休伯曼这样的人,正在把我们学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用于营销,”爱荷华大学神经学副教授南达库马尔·纳拉亚南(Nandakumar Narayanan)说。
© Jonathan Knowles/Getty Images
在多巴胺迷恋的潮流中,确实隐藏着一些真相,但它的精确功能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从一种不起眼的神经递质到文化符号,多巴胺的演变更多地反映了我们集体想要控制冲动的愿望,而不是关于这种化学物质本身。
以下是我们实际了解和不了解的——关于多巴胺的信息,以及如何区分有用的建议和伪科学炒作。
发现多巴胺
“多巴胺可能是大脑中最著名的神经递质,”密歇根大学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说。“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背负着很多包袱。”
大约70年前,多巴胺还只是3,4-二羟基苯乙胺,一种存在于体内的化学物质,20世纪早期的科学家猜测它与心率和血压有关。1952年,这种化学物质得到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名字:多巴胺。
© James O’Brien
20世纪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多巴胺只不过是一种去甲肾上腺素的半成品[2],而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与战斗或逃跑反应有关的激素。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德裔英国生物化学家赫尔曼“休”布拉施科(Hermann “Hugh” Blaschko)注意到多巴胺储存在大脑中[3],因此它不仅仅是另一种化学物质生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瑞典药理学家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进行了实验,确认多巴胺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但他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它在大脑中的具体作用[4]。
对帕金森病的平行研究带来了突破:神经学家意识到,这种疾病的震颤和肌肉僵硬,与控制运动的中脑部分多巴胺生成细胞的丧失有关。左旋多巴(L-DOPA),作为治疗帕金森病的“神奇药物”,于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曾经让无法动弹的患者暂时重获新生[5]。
多巴胺首次受到关注,激发了更多的制药研究。常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氟哌啶醇(Haloperidol)1958年首次进行了临床试验——它有效地治疗了精神疾病,但科学家们并不其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大脑中多巴胺受体的发现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氟哌啶醇与某种特定类型的多巴胺受体结合并阻断该受体,这表明多巴胺——特别是过量的多巴胺——在精神分裂症中起着核心作用。
多巴胺与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不断在临床研究中出现:成瘾、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抑郁症似乎都与多巴胺系统的变化有关。像阿得拉(Adderall)和利他林(Ritalin)这样的ADHD药物,以及成瘾性药物,如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都针对多巴胺系统,暗示它与习惯形成、渴望和欣快感有关。
© SciTechDaily
这些结果共同引发了我们对多巴胺理解的范式转变:如果这种化学物质与注意力和思维障碍有关,那么它必定在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与多巴胺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多巴胺信号,而多巴胺又会影响我们的感受,那么优化就大有可为。如果多巴胺对我们不经意间的行为做出反应,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改变生活方式来微调我们的多巴胺系统。
多巴胺是如何工作的?
尽管它是神经传递中的明星,但多巴胺也只是大脑众多化学信使之一。
只有极小一部分神经元能产生多巴胺:大约40万个神经元,占860亿个神经元的0.000005%。多巴胺生成神经元主要集中在中脑,它们在动机、学习和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功能都属于广义的动作选择范畴:权衡选项、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以及是否值得去做,并向大脑的其他部分发送指令。
无数的社交媒体视频会强调“多巴胺水平”:从性、锻炼身体到创造性表达,一切都会让多巴胺水平激增;而当你悲伤或缺乏动力时,多巴胺水平则会下降。
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解释。
西北大学神经科学家塔利亚·勒纳(Talia Lerner)告诉我,“(多巴胺)可要比简单的上升和下降复杂得多。”
多巴胺神经元从大脑的很多区域接收输入:你的感官系统、运动系统和边缘系统都会向中脑发送信息。勒纳说:“其中一些输入是根据你的需求来校准你获得的多巴胺量。”她强调,由于多巴胺神经元在不同的时间向不同的地方发送信号,“并不是只有一种多巴胺信号。”
© It's Nice That
多巴胺信号主要有两种类型:当神经元对某些特定刺激做出反应时,多巴胺会释放出来。但这些神经元也会在后台不断地发送信号,维持一个全天波动的基线水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家库尔特·弗雷泽(Kurt Fraser)告诉我,大脑中的多巴胺量一直在波动,但“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高’或‘低’多巴胺状态”。
要理解多巴胺释放后实际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必要先了解它不做什么。
我采访过的所有神经科学家都明确指出:多巴胺不是一种“快乐”化学物质。明尼苏达大学神经科学助理教授阿里夫·哈米德(Arif Hamid)表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多巴胺能让我们感觉良好,但“这一假设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推翻了”。
“如果非要给多巴胺贴上标签的话,”弗雷泽说,“我会说它就像是你欲望的化学物质。”但这不是抽象目标导向的欲望,比如渴望在工作中升职。它是一种更紧迫、几乎是动物性的欲望:当你吃零食、查看Instagram通知或抽烟时的那种感受。
© Harvard Health
它的确切功能甚至令许多神经科学家感到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确实认为多巴胺代表快乐——毕竟,当快乐的事情发生时,多巴胺就会释放出来。“如果你走出去,世界在召唤你,与人的互动很有趣,你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显然在做出反应,”贝里奇告诉我,“它让世界变得诱人。”
大约30年前,贝里奇进行了一系列关键实验[6],他的研究小组阻止实验室小鼠产生多巴胺,并观察了其后果。没有多巴胺,小鼠甚至无法自主移动来进食。但是,当人工用手喂给它们美味的东西时,小鼠仍然很享受。此后,类似的行为在人体实验中得到了重现。
因此,即使没有多巴胺,人们仍然可以享受快乐的事物;神经科学家怀疑,愉悦的感受本身,至少部分是由大脑中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称为内源性阿片类药物)介导的[7],这些化学物质与合成阿片类药物(如羟考酮)结合到相同的受体上。
多巴胺的作用,是让你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现在人们认为,它在激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脑做出决定并向身体发出指令时为大脑加油打气。除此之外,哈米德补充道,“它还是一位非常棒的教练”,教我们如何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
大约在贝里奇和同事研究多巴胺缺乏小鼠的同时,德国神经科学家沃尔夫拉姆·舒尔茨(Wolfram Schultz)的团队记录了猴子伸手去拿零食时多巴胺细胞的活动,希望更好地了解帕金森病。结果,他们注意到了彻底改变我们对多巴胺理解的东西:多巴胺神经元不是对零食本身作出反应,而是对打开零食盒的声音作出反应[8]。一旦猴子熟悉了这项任务,它们的多巴胺神经元就会完全停止放电。
换句话说,多巴胺是对惊喜作出反应——而非奖励本身。这种信号被称为“奖励预测误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s),它告诉大脑其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对于试错学习至关重要。
多巴胺涉及动机和学习,但这两者不非孤立存在的。动机会让你集中注意力去学习,你也可以学会激励自己去做某事。霍奇基斯脑研究所(Hotchkiss Brain Institute)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妮·博格兰德(Stephanie Borgland)告诉我,比如,多巴胺神经元会向前额皮质发送信号,帮助你弄清楚应该关注什么。多巴胺还推动习惯的形成,这是我们学会被激励去做的行为,比如在渴望社交认可时查看Instagram的新通知。
© BRIAN STAUFFER
问题在于,博格兰德说,“你的大脑并不知道它是在发展一种新技能,还是即将形成一种坏习惯。”
一旦养成习惯,它就不再受多巴胺系统的控制——这可能导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与我们想要的事情之间的裂痕。这就是为什么有药物滥用障碍的人会被迫使用毒品,却无法从中获得快感。像诺和泰(Ozempic)这样的新药,作用于接收多巴胺信号的神经元,将渴望降低到更易于控制的强度。
成瘾和多巴胺之间的深层联系,使得这种化学物质很容易成为自助指南的目标,可以“优化”它以促进与药物、工作建立更健康的关系。但博格兰认为这大多是“胡扯”。她也并非唯一持此看法的人。
多巴胺排毒和禁食:这都是真的吗?
随着多巴胺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这种化学物质开始出现在电影、音乐和文身潮流中。2014年,我就让一位朋友在我身上刺了一个多巴胺分子文身。
现如今,多巴胺被休伯曼和畅销书《多巴胺国度》(Dopamine Nation)的作者安娜·伦姆基(Anna Lembke)等名人科学家视为大多数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通常是认知行为疗法、工程优化和Goop式“健康”的一套奇怪组合(Goop,好莱坞女星温妮丝·帕特洛创立的品牌,从Goop创立之初,帕特洛就经常与用户分享一些当时极为冷门的健康知识和保养方法,其中有的逐渐风靡全球,使Goop成为了不少女性群体中的“保健圣经”。Goop也是健康饮食、营养减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编者注)。
尽管如此,我采访过的所有神经科学家都对媒体关于多巴胺的描述感到不满。当被问及休伯曼和其他有影响力人士提供的健康建议时,纳拉亚南说,他们简化了复杂的话题,“对科学和公众都造成了伤害”。
比如所谓“多巴胺禁食”(Dopamine fasting)的潮流趋势。它指导人们有意识地远离那些可能引发多巴胺释放的、可能会成瘾的事物,可问题在于,单凭一种化学物质无法彻底改变你的心理健康。
在许多情况下,对多巴胺的强调似乎更多是语义上的,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当人们把“多巴胺”附加到几乎任何事物上时,他们通常只是讨论习惯、成瘾和控制,并使用神经科学术语来增加科技含金量。例如,多巴胺禁食本质上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只不过用“多巴胺”作为寻求快乐的隐喻[9]。卡梅隆·塞帕(Cameron Sepah)在2019年发布了一份广为流传的多巴胺禁食指南,他甚至告诉《纽约时报》,这其中的“多巴胺”不应按字面理解——但它“是个吸引眼球的标题”。
但如今我们许多人求助于多巴胺技术来摆脱冲动,尤其是与屏幕时间有关的冲动,这是有原因的。2010年代末,像多巴胺实验室(Dopamine Labs,现已解散)这样的初创公司公然利用多巴胺来推销神经营销策略,帮助科技公司利用大脑的奖励系统让消费者沉迷于他们的平台。
神经科学家认为,手机应用的设计就是让人养成习惯,“它可能确实会激活你的多巴胺系统,”勒纳说。Instagram和Hinge等应用会按照可变的奖励时间表发送通知和热门匹配,就像老虎机一样。
如果你的大脑无法预测奖励何时到来,那么每次提醒都会让人感到意外:这是通过多巴胺发出的正向奖励预测误差信号。勒纳澄清说,这些应用不一定会让你的整体多巴胺水平升高或降低,但它们是为了强化你的滑屏行为而设计的。
但弗雷泽表示,说这些多巴胺的累积最终会让我们无法体验快乐,这有点儿牵强。多巴胺断食等潮流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过度沉迷于强迫性享乐主义行为会导致多巴胺“耗尽”,但这与人类多巴胺释放的时间尺度并不完全一致。
© The Villanovan
穿着鲜艳有趣的衣服来提升情绪等“多巴胺穿搭”趋势,也过于依赖多巴胺来解释具有许多潜在原因的事情。博格兰德怀疑,“穿着你最喜欢的衣服可能会调节一大堆不同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包括血清素(其产生和释放的过程与多巴胺完全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神经递质。”
纳拉亚南举了个例子:如果你买了个纸杯蛋糕,吃了它,而且它很美味,多巴胺肯定是参与这种体验的一部分。“但把这种纸杯蛋糕体验简化为多巴胺药丸是行不通的,”他笑着说,“事实上,它会让你呕吐。”(恶心是拟多巴胺药物的常见副作用)
你的大脑不仅仅是一个装满多巴胺的油箱。你不能简单地通过补充它来提高你的情绪、工作记忆或注意力。心理健康、生产力和多巴胺信号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大脑化学物质如何影响我们的感受,但勒纳相信,“至少我们可以说,问题不在于你的多巴胺是‘太高’还是‘太低’,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神经科学家对多巴胺的了解比对许多其他神经递质的了解要多,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去年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汇集了数千名脑科学家,会议中进行了数十场与多巴胺相关的演讲。哈米德说:“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阶段,我们开始意识到多巴胺参与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完全认识到的过程。”
© Simon Bailly / Sepia
为什么“快乐化学物质”的概念会引起我们的共鸣?
几十年来,我们都知道多巴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快乐化学物质”,但流行文化仍然将其描绘成快乐化学物质。就连弗兰克·穆迪(Franc Moody)2018年的歌曲《多巴胺》也以科学准确描述多巴胺合成作为开场,用多巴胺来比喻舞池里的享乐主义辣妹。
贝里奇说,我们对多巴胺的过时理解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神经科学家仍然会犯错。“他们会写出只有在多巴胺是快乐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的短语,”他笑着说,“我认为这是他们以前的自我在作祟。”
也许这个概念引起共鸣的原因与其他曾经是临床概念的词语(如失调)类似: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可以说过于明确的)框架来理解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将多巴胺想象成一个杠杆,拉动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想象潮起潮落,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感到精力充沛或心不在焉,我们就会重新获得一种掌控自己思想的感觉。然而,多巴胺在我们大脑中的运作实际上更加微妙和神秘。
弗雷泽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时常引用多巴胺,“是因为人们对多巴胺的了解已经足够多,我们谈论它,就好像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一样。”但他担心,“多巴胺只是一个稻草人”,让有些人有理由声称他们知道如何控制我们的大脑。为这种观点埋单的大有人在。随着我们继续和注意力进行一场节节败退的斗争时,我们需要主动权,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分散注意力的时代。我们都有智能手机,有人担心它们正在毁掉我们的大脑。随着我们在TikTok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新闻在缩短,歌曲也在变得越来越短。
虽然我们浏览访问的内容数量和便利性都是新事物,但寻求分散注意力并非我们这个多巴胺意识时代的独有现象。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摆脱日常生活平庸和焦虑的方法。早在17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就写道,想要分散注意力是完全自然的,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不例外:“国王身边的人只想着如何取悦他,不让他思考自己。因为即使是国王,如果他思考自己,也会感到不快乐。”
一旦我们开始分神,我们便想着要努力摆脱这种状态。数千年来,冥想一直根植于许多精神信仰体系,作为寻求启迪的一种方式。
以优化为导向的内容创作者理查德·杨(Richard Yong,在YouTube上拥有357万粉丝,名为Improvement Pill),他告诉《旧金山纪事报》:“多巴胺断食基本上就是一个简易版本的内观禅修”,一种专注的、高强度的冥想练习。从不那么极端的角度来看,在睡觉前几个小时刻意戒除查看手机等行为似乎是常识(也是好建议!)。只有当你试图将这些行为变化与单一神经递质直接联系起来时,情况才会变得奇怪。
多巴胺已经成为它试图解释的一切的副产品:冲动、成瘾、我们对优化的动因。正如技术和文化学者L·M·萨卡萨斯(L.M. Sacasas)所写:“它是一个强大且引人注目的模因,尽管它以最好的面貌呈现。出于这些原因,我担心它可能会把我们困在它试图克服的模式中。”
文/Celia Ford
译/tim
校对/tamiya2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im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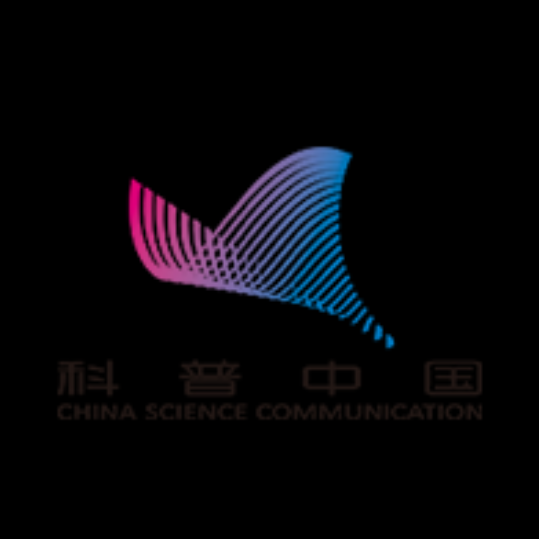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