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着,盼望着,酷暑终于要走了……“立秋”的到来和“末伏”的结束让我们已经可以从高温里得以喘息。而很快,阳光就会从“人人避之而不及”变成大家都渴求珍惜的东西。
多数人对于太阳的感情都因温度和环境而不断变化,“冬喜夏恶”,大致如此。但偏偏就有这样一个人,执着地“爱”太阳长达半个世纪,始终如一。在他眼中,无论是“黑子耀斑”还是“磁暴极光”,都是太阳偶尔迸发的“小情绪”,他极其乐于也擅于执笔将其转化为可读、可讲的科学道理。
他叫汪景琇,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他已经“追”太阳近一生。如今他年过耄耋,依然在太阳物理学的科普一线,笑意盈盈地告诉每位向他提出问题的人:太阳活动密切影响着人类家园。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景琇
笑眯眯的“电子爷爷”
“太阳常常在微笑,但偶尔也会烦闷、暴躁甚至狂怒。”“极光其实就像太阳打个了喷嚏。”……在社交平台上疯狂圈粉数十万,汪景琇十分擅长回答各类脑洞大开、奇奇怪怪的科学问题。即便是懵懂孩童向他提出诸如“太阳是不是个气球?太阳会呼吸吗?存在第二个太阳吗?太阳的寿命是多少?”之类的问题,这位科学巨匠也总是笑眯眯地在视频中作出深入浅出的科普和解答,并且会在视频封面亲切地标注上“答小朋友提问”几个字。

汪景琇的社交平台
于是,在汪院士的评论区,总会出现“除了汪爷爷谁还会把我们当孩子啊!”“谁懂啊,他叫我‘小朋友’!”“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明星’!”之类的言论,因为人们能够真切感受到科学家的“烟火气”,而这些恰恰得益于汪院士在专业理论上的深厚积淀与不懈努力。
1944年5月,汪景琇在辽宁抚顺出生,家中排行第四。祖父和父亲都有任教经历,成长于读书氛围浓厚的家庭,他很小就展现出读书方面的天赋,且奋学笃行,以汲取知识为最大欢喜。1963年,19岁的汪景琇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实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而彼时他想,“要当科学家”是第二个。
受家庭原因影响,在填报专业时,汪景琇很谨慎:“我当时选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我的第一志愿可能会写原子核物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怀着无限憧憬与希望在逐梦之旅上再次扬帆起航。
6年大学生活的记忆(当时北大理科学制6年)被汪景琇融在一首名为《走进北京大学》的诗里,他写“告别了北方迷人的雪夜和眷恋的山野春光/走向那庄严的青年时代/那广阔生活的海洋/怀着激情、欢乐和幸福/怀着年轻人金色的理想/带着祖国交给的神圣使命/走进我最向往的科学殿堂”以纪念未名湖畔、图书馆中的苦读岁月,这也是让他至今都很怀念的“一段最美时光”。
1969年,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汪景琇大学毕业了。随后1970年3月,他被分配到了辽宁抚顺清原。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汪景琇先后在这里专心做一名农村中学教员和气象站观测员。直到1978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汪景琇对科学研究的向往再次被点燃。得益于在北京大学打下的良好的知识基础,汪景琇顺利考上了北京天文台的硕士研究生。
此后,汪景琇又攻读了博士研究生,终顺利留在中国科学院当研究员,从小立下的“当科学家”的梦想终成现实,“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期间真正学习科学知识的时间很短,所以一旦能够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就会感到很幸运。”他说。
“顶天立地”的中国学者
“银河中三千亿颗恒星,太阳只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但是越是普通,它越重要。为什么?因为研究了太阳之后就会知道恒星是什么样的。”在一次给学生的科普讲座中,汪景琇分享了太阳研究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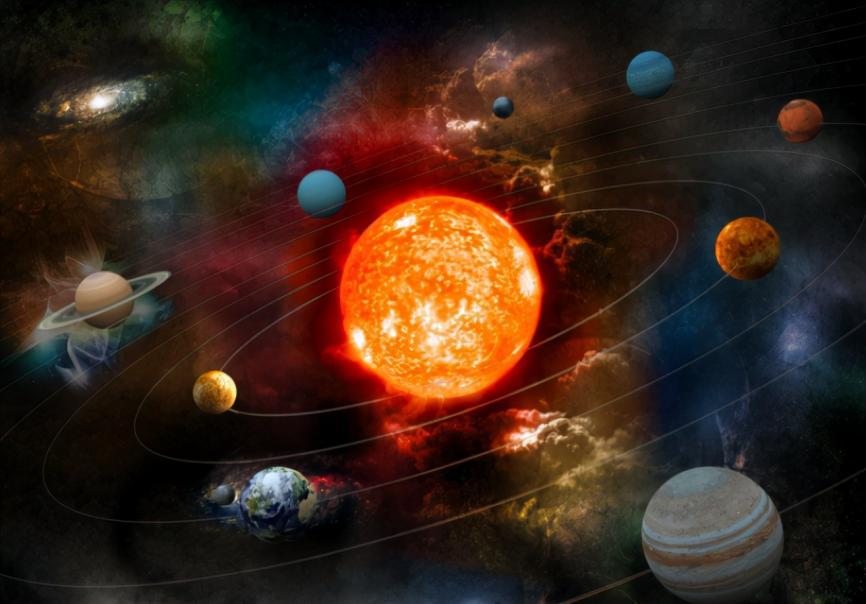
太阳在太阳系中
而研究生时期的汪景琇,其实也就如太阳一般“普通”。首先,与太阳研究的结缘只是汪景琇凭直觉的一次选择,“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后,因为我对恒星、太阳、星系、宇宙学都不太了解,只觉得太阳离我们近一点儿,再加上之前在农村做过5年的气象员,觉得太阳跟天气、气候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就选了太阳物理”。
但很快汪景琇便发现“研究生课程真的很难”,难到“听不懂”也“跟不上”。再加上身边许多授课老师都是业内的执牛耳者、大师级学者,比如彭桓武院士,从不会因为个别学生“听不懂”而降低授课标准。
怎么办?只有磨。英文文献看不懂就疯狂背单词,理论基础打不牢就手动推导公式、反复请教恩师……终于,和导师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了3篇文章之后,汪景琇生出了一些信心。1983年,汪景琇决意开拓国际视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学。
“其实当年我们国家的太阳物理学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国际上传播的成果和数据也比较少,但我就憋着一口气,我想证明我们中国学者一点儿不比别人差!”汪院士说到也做到了。后来,他成功测量出了太阳表面最小可测磁元的磁通量,并和导师史忠先先生一起为加州理工学院的磁像仪做了定标、借助加州理工学院先进的观测设备观测太阳……访学结束后,汪景琇还进一步开展了“日不落的联测”等研究活动,且组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门学术会议……使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逐渐走向国际前沿。
“没齿而无怨言”
然而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汪景琇的白发与皱纹在一日日的观测、研究中悄然生长,转眼他也来到了“应该退休”的年纪。但科学没有终点,奋斗更无尽头。于是这位矍铄老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科普教育。
面对镜头与媒体,汪景琇不止一次提及,自己对科普工作的责任感多源自恩师王绶琯院士的影响。“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绶琯院士,以他的报国之志、赤子情怀,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所以这种科学精神我不但要学下来,还要用它来教育我的学生。”
1999年,王绶琯倡议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致力于培养“明天杰出科学家”。“当我看到已经90多岁高龄的敬爱的导师,仍然参加青少年俱乐部‘科技实践’的评议活动和俱乐部委员会的会议,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汪景琇如是说。此后在接到俱乐部评议活动的邀请时,哪怕是周末、哪怕要占用一整天,他也会如期到场。

汪景琇为中学生签名
“我希望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是璀璨的,是闪耀的,是向阳而生的,是创造未来的。为达此愿,我没齿而无怨言。”尽管汪景琇的日程表已经排得很满:参加“院士专家讲科学教育特别行动”、担任北京市大峪中学科学教育校长、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评议活动……但只要是给孩子们做科普,他总会挤出时间,甚至亲自撰写PPT,还会根据受众的年龄段加以调整。
1965年,21岁的汪景琇曾在北京大学写下一首诗,题为《我愿意》,“我愿意/终生工作在实验室里/默默地勤奋耕耘/直到停止呼吸……我愿意/一生一世不停息/洒尽青春的血泪和汗水/去灌注科学的园地……”
2024年,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容颜虽老但初心犹在的汪景琇仍端坐在桌前孜孜不倦,分析数据、撰写论文……就如同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太阳一样“燃烧心脏”,以知识的光辉照耀每一寸他深爱的地方。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