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乔和第N代人
小沃尔特·M.米勒 著|轮轴 译 杨枫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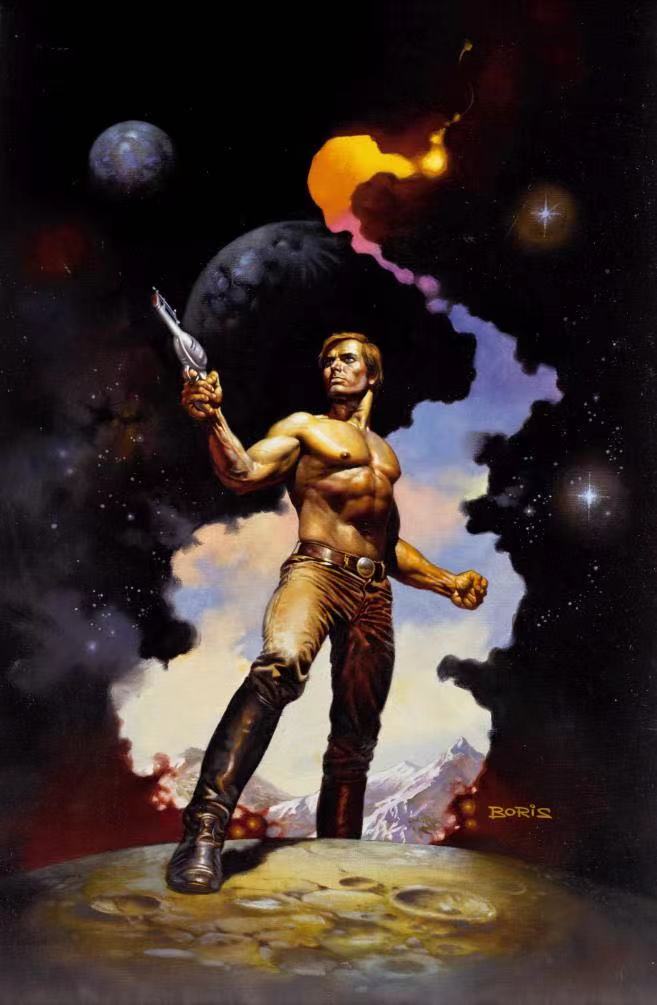
一个盗贼,将像盗贼一样死去。
他用手腕吊在杆子上,苍白的阳光在他裸露的脊背上衰弱地闪烁。他等待着,双眼紧闭,嘴唇缓缓蠕动。他的脸紧贴着粗糙的木头,踮脚站着以期缓解肩部越发强烈的疼痛。当他的脚踝痛到难以忍受,他就靠着手腕上方刺穿他前臂的长钉吊住自己。
他还很年轻,可能才刚度过第十个火星年,他黑色的短发被修剪成单身汉的样子——那些还没有孩子或者至少并未承认自己有孩子的人常留这种发型。他体态柔韧优美、肌肉结实、四肢修长,宛如一只半饥半饱的野兽,怀着饥饿的怒火,伏低身躯准备伏击。他的面孔,尽管在痛苦与恐惧中扭曲,仍存留着年轻人的自大。
当他睁开眼,便能看到火星的土丘在阳光中曝晒,在树木的笼罩下显出灰绿色调——那是上古圣父们从天堂赐下的树木。他亦能看到离他不远处的刽子手,叉开腿坐着,平静地咀嚼着一片草叶,等待着行刑。那是一个矮胖的宽脸男人,间或用空洞的蓝眼睛瞥一眼窃贼,同时又随意地将放血刀向地上扔着玩。他的目光中空无一物。
“准备好让我‘处理’你了么,阿斯尔?”刽子手嘟囔着,却显得并不太厌倦。
尽管刽子手处于“射程”之外,阿斯尔仍然向他啐了口唾沫,并试图在杆子上擦擦他的脸。“你这狗娘养的!”他含糊不清地抱怨。
刽子手轻声一笑,接着扔刀子玩。
在贯穿他手臂的尖钉上吊了三个小时之后,阿斯尔感到自己的体力不断衰弱,太阳穴一抽一抽地疼,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带来一阵新的痛苦。粘稠的鲜血已经不再沿着他的手臂淌下——那些人一定懂得怎样“恰到好处“地将钉子扎入囚犯的身体。但他脑中回荡的心跳正如重锤敲击铸铁。
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次心跳——如今的他又还剩多少次呢?
他呜咽、扭动,开始失去一切希望。玛拉已前往拜访议长,向他祈求饶恕这个窃贼的性命——但玛拉可能还不如一只野生希芬(?)可靠,他仿佛看到那两人在托克拉的别墅中,一边喝着琥珀酒一边咯咯直笑,而年轻盗贼的生命则缓慢枯竭。
阿斯尔毫无悔意。对他而言,他的父亲是一个变节者,为了购买妻子挥霍了最后一条仪轨公式,随后便一贫如洗,并将他的妻子带去了山中。阿斯尔在山中出生,但再次回到先人曾居的村庄,在那里一边作佣人,一边窃取他主人们的仪轨。但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一个仪轨窃贼在社区中引发了巨大的混乱。一个圣语的主人,在不知道圣语被盗的情况下,试图将圣语花掉,最终会有人提出反诉,到那时总会计官必须被召来。而窃贼终会落网。
阿斯尔盗走的不仅是财产,更是支撑人们灵魂的力量。因此他们钉穿他的手腕把他吊起,等着他祈求自己的处刑。
女人想老公,
男人想老婆,
小孩想喝奶,
小贼想挨刀……
这是一首他童年时的韵律,一段幼稚的歌词,一个用来决定谁先从产蜜仙人掌中饮蜜汁的儿童游戏。他呻吟着,移动着他的重心,企图让自己更舒服些。玛拉在哪儿?
“准备好让我给你来一刀了么,阿斯尔?”矮胖的刽子手问道。
阿斯尔因憎恶而对他眯起了眼。根据法律的约束,刽子手必须等待受刑者祈求被处刑。但阿斯尔不知道他的命运会走向何方。家族长老会秘密地审判了他,在判决中决定了他究竟要受到刽子手怎样的刑罚。但阿斯尔并不知道判决的内容。他只知道当他祈求处刑,刽子手就会拿着放血刀上前来施加刑法,按照判决夺走他的生命或他的肢体。或许他只会失去一只眼睛、耳朵,或手指。也可能更糟,他会失去自己的性命、双臂,或是他男性身份的证明。
除非他祈求处刑,他便无法获知他的刑罚。如果他拒绝祈求,便会被一直悬挂。照理来说,在被悬挂四天,刽子手拔出钉子后,盗贼便能逃出生天。有时,犯人的确能撑过四天,但当钉子被拔出后,就只剩下一具尸体瘫倒在地。
西沉的太阳刺痛了阿斯尔的眼睛。阿斯尔理解太阳,理解那愚蠢的议会所无法理解的事。一个成功的窃贼会一次次被赋予智慧,因为他所铭记的财富多过二十个老实人的总和。那是上古众神的话语——费米、爱因斯坦、埃格曼、豪斯与无数其他神祗——大多数人只拥有一些无意义的散碎的圣语。但窃贼会记住他窃听的交易中所有的圣语,无数的语词将拼合成真正有意义的思想。
阿斯尔如今懂得,曾经死寂的火星今日正再次死去,大气正再一次向太空逸散。人们将随之一起灭亡,除非有人抓紧时间做些什么。地底的巨风之火必须被再次点燃,但已无人知晓该怎样去做。诸部落在无知中沉沦,尽管圣书已有预警:
我们意识到,火星殖民者在没有基本工具的情况下,无法维持技术的存在,而对技术的重建将需要数代人在智慧的领导下做出的努力。若能保有知识,那么在欲望的不断鼓动下,殖民者们或能复原我们的机器文化。但如果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N代人都未能推进这一逐渐发展工具技术的进程,那么知识也会变得毫无价值。
这些话语来自名为罗金斯的神明,来自名为《火星文化的发展》的典籍,他从许多地方窃来它的碎片。典籍本身已不复存在,而话语只存在于仪式祷文之中,作为财富被占有。
阿斯尔感到无比不适。痛苦与缓慢的失血使他浑身虚弱、视线模糊。直到他听到她的脚踩过干草时发出的沙沙声时,他才意识到她的到来。
“玛拉——”
玛拉轻蔑地一笑,向着杆子地下鄙视地吐了一口唾沫。她是一位家族长老的女儿,身材高挑苗条,举止傲慢,眼神中藏着嘲弄。她抱着双臂站了一会儿,仿佛消遣一般看着阿斯尔。随后,她的一只眼睛缓慢而庄重地眨了一下。她转过身去,向刽子手发话。
“我能逗逗这个囚犯么,斯卢比?”,她问道。
“禁止对窃贼说话。”刽子手用低沉而粗野的声音说道。
“他准备好祈求正义的处刑了么,斯卢比?”
刽子手咧嘴一笑,望着阿斯尔:“准备好让我给你来一刀了么,小贼?”
阿斯尔发出嘶嘶声试图侮辱对方。那个女孩背叛了他。“他显然是个懦夫,”她说。“或许他打算被吊上四天。”
“那就让他挂在那儿吧。”
“不——我想我还是想看他求饶。”
玛拉用一种搜索式的眼光久久地看了阿斯尔一眼,然后背过身去走开了。盗贼轻声咒骂着她,用眼睛追踪她远去的身影。走出十来步后,她再次停了下来,转过头来,又慢慢地眨了一次眼。随后,她便向她父亲的房子走去了。玛拉的眨眼一时间让阿斯尔头皮发麻,但随后……
或许她没有背叛我?或许她已经从托克拉那里套出了判决的内容,已经知道了他会经受怎样的刑罚。“我想我还是想看他求饶。”
但另一方面,这个喜怒无常的女魔头也可能是在欺骗他,想让他去祈求一份她早已知道会为他带来死亡或肢解的刑罚——只为了给她自己取乐。
他在心里又骂了几句,发着抖看向百无聊赖的刽子手。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一边抵抗晕眩一边试图组织语言。斯鲁比听到他的低于,抬头向上看去。
“你准备好被处刑了么?”
阿斯尔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那你就来吧!”他突然大叫道,用杆子撑住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不呢?拖延处刑也只能为自己挣来一点甚至不算活着的时间。让这一切结束吧。与这样的耻辱相比,永恒的长眠也显得甜美非常。最后的一刀会带来解脱。
他听到刽子手轻笑着站了起来,听到脚步缓缓逼近,听到斯鲁比极快地将放血刀挥出弧线时,刀刃的嘶嘶声犹如鸣唱。刽子手一步步向他靠近,金属在他身边划过空气的哨声戏弄着这个囚犯。阿斯尔理应开始祈求。刀刃时不时紧贴着他的皮肤,却在片刻后被再次取走。然后,阿斯尔听到刽子手的衣袍沙沙作响,他的手臂正伸向后方。阿斯尔睁开了双眼。
刽子手狞笑着,高举利刃——正瞄准了阿斯尔的头!玛拉骗了他。他呻吟着,再次闭上了眼,低声念诵起一段已记不清晰的祈祷。
一刀斩下——利刃扎入他头顶的杆子中。阿斯尔昏厥过去。
当阿斯尔醒来时,他正浑身瘫软躺在地上。刽子手踢了他几下把他翻了过来。
“鉴于你年纪还小,小贼,”刽子手粗鲁地低声说道,“长老会下令你将被永久放逐。现在是黄昏,到黎明时分你必须离开到山中去。如果你敢再回到平原,就把你捆到一头野生希芬身上,把你在地上拖死。”
阿斯尔虚弱地喘息着,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了一道崭新的伤口,刻意为了留下疤痕而用铁锈抹过。斯鲁比给他打上了放逐者的烙印。但所幸除了他前臂上钉子留下的孔洞,他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他的双手已经麻木,手指也动弹不得。斯鲁比已简单包扎了钉子留下的伤口,但绷带已经血迹斑斑,甚至向外渗血。
刽子手走后,阿斯尔无力地慢慢坐了起来。几个镇民站在附近,窃笑着。他忽视了那些人的嘘声,跌跌撞撞地向十分钟路程外的村庄外围走去。他必须和玛拉谈谈,再和她父亲谈谈——如果那个顽固的老不死真的肯听。他的盗贼生涯带来的知识重重压在他的身上,蔓生出绝望与恐惧。
当阿斯尔到达韦尔科尔家宅时,夜幕已经落下。在街上,人们向他吐口水,其中一些还在他经过时,向他身上泼出一把把尘土。
透过韦尔科尔家的门缝,一点火光微弱地闪动。
阿斯尔敲了敲门,静静等待着。韦尔科尔长老拿着提灯打开了门。他把灯放在地上,双腿岔开站着,两臂抱在胸前,傲慢地瞪着盗贼。他的面容像饱经风的顽石般坚硬。他什么也不说,就那样轻蔑地站着。
阿斯尔低下头。“我有事情要来恳请您,长老大人。”
韦尔科尔带着嫌恶哼了一声。“恳请我收回我们对你的仁慈么?”
阿斯尔立刻抬起头,摇了摇头道:“绝对不是的!对您的仁慈我感激不尽。”
“那你想说什么?”
“在我还是个盗贼的时候,我曾获得过许多知识。我知道这个世界在走向死亡,空气正飘散到天空中去。我希望长老会能知道这一点。我们必须研读上古众神的话语,重现祂们的神迹,否则我们孩子的孩子就注定要在枯竭的世界中窒息。”
韦尔科尔又哼了一声。他捡起灯。“听从盗贼的知识者要受诅咒。按那知识行事之人其诅咒倍增,是那罪恶的一份子。”
“在墓穴里,”阿斯尔坚持说。“重启巨风之火的钥匙就在墓穴里。神明罗金斯已在他的话语中启示我们——”
“闭嘴!我不想听你的鬼话!”
“那好吧,但火焰可以被重新点燃,大气也能得到补充。在墓穴里——”他用力敲了敲自己的头,又摇摇头。“我必须告诉长老会这件事。”
“长老会什么也不会知道,而你必须在黎明前离开。墓穴被名为大乔的沉睡者守卫着,胆敢进入就意味着死亡。现在滚吧。”
韦尔科尔后退几步,“砰”的一声摔上了门。阿斯尔因受挫而分外消沉。他瘫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了一下。夜晚漆黑如墨,唯有窗口灯光间或闪动。
“嘘!”
从影子中发出了声响。阿斯尔立刻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源头。
“嘘!阿斯尔!”
是玛拉,韦尔科尔长老的女儿。她从房屋后边溜了出来,在转角处盯着他。阿斯尔静静地站起来,向她走去。
“斯鲁比对你做了什么?”玛拉小声说。
阿斯尔喘息着,愤怒地抓住了她的肩膀。“这种事你难道不知道么?”
“别这样!停下!你弄疼我了。托克拉不肯告诉我。我都已经向他示过爱了,但他还是不肯说。”
阿斯尔怒骂了一句,放开了她。
“你可能得花点时间消化一下情况”,玛拉小声说道。“我知道如果你再等下去,就会在悬挂中变得太虚弱,而没有体力逃跑了。”
阿斯尔又对着玛拉骂了几句粗话。
“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她呵斥道。“亏我还给你买了一头希芬!”
“你买了什么?”
“托克拉送了我一条仪式圣语,我用它给你买了一头希芬。你也知道,你不可能徒步就走到山中去。”
阿斯尔的怒火熊熊燃烧。“你和托克拉睡过了!”他怒骂道。
“你这是在嫉妒么?”玛拉窃笑道。
“我怎么会嫉妒!我一看到你就心烦!”
“那好吧,那头希芬我就留下了。”
“随便你吧!”他低吼道。“我也用不着他,因为我可不会到山中去!”
玛拉倒吸一口冷气。“你这蠢货,你必须逃跑。他们会杀了你的!”
阿斯尔转过身去,感到有些不适。玛拉抓住他的手臂,试图把他拉回来。“阿斯尔!带上希芬赶快跑吧!”
“我会走的”,阿斯尔低声说。“但我不到山中去,而是要到墓穴中去。”
他怒气冲冲地走了,但玛拉仍然一路小步跑着跟上他,试图把他拽回去。“蠢货!墓穴可是神圣之地!牧师们守卫着入口,还有沉睡者守护着内门。如果你试图闯入的话,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而且如果你逗留于此,到了明天长老会也会把你杀掉的。”
“那就让他们杀了我吧!”阿斯尔几乎是在咆哮。“我可不是那种只会哭鼻子的镇民!我来自山中,我的父亲是个叛徒。你们的长老会无权审判我。现在是我来审判他们!”
这些话带着愤怒迸发而出,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么做的愚蠢。他料想玛拉会轻蔑地指责他,但她仍拉着他的手臂,试图祈求他离开。阿斯尔拖着她已经走出十几栋建筑的距离。玛拉的声音已经失去最初的傲慢,只剩下恳求。
“求求你了,阿斯尔!快离开这里吧。听着!我甚至都可以和你一起走——如果你想的话。”
阿斯尔冷笑起来。“我可不想捡托克拉用剩下的。”
玛拉狠狠地扇了他的嘴。“托克拉就是个无能的、连走路也走不稳的老东西。他得了关节炎,动都快动不了了。你这个白痴!我不过是坐在他的腿上,替你亲了亲他的秃头。”
“那他为什么要送你仪式圣语呢?”他生硬地问道。
“因为他喜欢我。”
“你在撒谎。”阿斯尔愤怒地向前大步走去。
“那就这样吧!你就到墓穴去吧。我会告诉父亲,他们会在你抵达之前就抓住你。”
玛拉放开阿斯尔的手臂,停下了。阿斯尔顾虑了一下。她说这话是认真的。他慢慢走回到她身前,把他肿胀的双手环在玛拉的脖颈上。她一动也不动。
“那我不如现在掐死你,让你冰冷地躺在这里吧。”他说这话时,声音几乎像一条蛇。
玛拉的脸被笼罩在黑暗中,但他还是能看到她脸上冷静的笑容。
“因为你爱我,弗兰尼克的阿斯尔。”
他松开手,又低声骂了几句。玛拉轻声一笑,拉住了他的手臂。
“来吧。我们去拿那头希芬。”
为什么不呢?阿斯尔这样想着。把她的希芬带上,把她也带上。他完全可以在村庄外几里处甩下她,再绕个圈回到墓穴。玛拉轻轻靠在阿斯尔的身上,两人就这样向玛拉父亲的房子走回去,然后绕过房子,悄悄进入那排房屋背后的田地。火卫一在西方低垂,黑暗的天幕中,那小小的圆盘只留下一点微弱的光亮。
当二人走向那笼罩在阴影中的庞大身形时,阿斯尔听到了希芬的呼吸声。随着那生物感知到他们的到来,它巨大的羽翼蛇行而出,发出了如同吹响长笛般的叫声。这是原产于火星的生物,与上古众神们从天界带来的生物毫无相似之处。它的后背覆盖着一层甲虫一样的薄壳,但腹部却多孔而柔软。它进食时,就坐在事物上面,将它吸收入体内。它的翅膀瘦骨嶙峋,皮膜被撑开在一副脆弱的骨架上。它没有头,也没有中央性的大脑,神经功能区域分布在身体各处。
当两人爬上希芬宽而平的背部时,这头巨兽几乎没有反应,它薄而坚硬的背甲已经被人切好了洞、穿上了带子,两人用那些带子固定了自己。希芬缓缓的吸入一大口空气,当它肺部巨大的气囊膨胀起来,两个骑手也随之被抬高。一只充气的希芬,其围长几乎能达到未充气时的四倍。在吸气之后,随着肌肉收紧,这生物的体型又开始缩小,开始压缩气囊中的空气,直到漏气的微弱嘶嘶声从身后传来。它等待着,双翼紧绷。
玛拉拽了一下安装在它身侧穿入肉里的圆环。随着一阵爆响,那生物猝然起动。大自然对喷气推进的实验产物向前腾飞,随后顺风而行。在第一口气耗尽后,它便再次吸气,将自身向前推进。整趟旅程忽动忽停。每次尾部喷气都会带来一阵剧烈的摇晃。随着希芬越飞越高,二人开始让它选择自己的方向。随后玛拉又拽了一下系在翅膀上的皮带,那生物就突然转向,向着远方黑暗的群山俯冲而去。
风如长鞭呼啸而过,阿斯尔坐在玛拉身后,脸上浮现出几分讥笑。他一直等待着,直到他们已飞出足够远,任何人的尖叫也不会被村中人听闻。随后,他轻轻地抓住了玛拉的肩膀。玛拉把这误认为是在表达爱意,向后靠在阿斯尔的身上,黑发披散在他的肩头。他吻了她——同时小心翼翼地摸索她腰带上挂着的小刀。他的手指有些僵硬,但最终还是将刀握在手中,用刃轻轻抵住玛拉的喉管。玛拉倒抽一口气。阿斯尔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她的头发。
“现在快让希芬着陆!”他命令道。
“你在做什么,阿斯尔!”
“快!”他大吼着。
“你要做什么?”
“把你留在这,我自己回墓穴去。”
“不!别把我在夜里留在这儿!”
阿斯尔犹豫了一下。在西米利安平原上有徘徊兽潜伏着,那些野兽会把这个从韦尔科尔家中逃出的女孩当作一顿幸运的加餐,或许还是它们很少能尝到的美味。在呼啸的风声中,他偶尔能听到夹杂着一阵长嚎,那是尖牙利齿的“好客原住民”在等待它们的晚餐。
“那好吧,”阿斯尔不情愿地低声说道。“向墓穴转向吧。但你只要敢叫一声,我就砍了你。”他把刀从玛拉喉咙上拿开,用刀尖贴着她的后背。
“求求你,阿斯尔,不要!”玛拉恳求道。“我们到山里去吧。你为什么想去墓穴呢?因为托克拉么?”
阿斯尔缓缓将刀尖刺入玛拉的衣服,直到她惊叫起来。“让托克拉去死吧,你也一样!”他低吼到。“快给我转向!”
“为什么?”
“我要下到墓穴中去点燃巨风之火。”
“你疯了!上古众神的魂灵就生活在墓穴里。”
“我要去点燃巨风之火,”他毫不动摇。“现在你要么调转方向回去,要么着陆,然后我一个人回去。”
在短暂的沉默后,玛拉拉紧了一条系在翅膀上的缰绳,希芬便在空中突然转弯。他们又飞了一里到了村庄的南方,然后又向更远处飞去——在那里的修道院中,敬奉大乔的牧师守卫着墓穴的入口。在修道院前的地面上,散布着一片微光。
“围着修道院绕一圈。”阿斯尔下令。
“你不能进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阿斯尔并不这么认为。除了为伟大的沉睡者献上小动物作为祭品的牧师以外,从没有人进入过墓穴。既然没有外人敢接近通向墓穴的竖井,那么守卫也不可能会预料到有人要来。阿斯尔并不认为他们能保持警惕。
修道院从上方看去是一个空心的方形,在庭院的正中立着一座小石塔。通往竖井的入口就位于塔楼之中。随着他们盘旋着向下,阿斯尔试图观察庭院中的情况,在火卫一昏暗的光中,映着从修道院窗户中透出的橙黄色火光,庭院似乎空无一人。
“在塔楼边着陆!”他命令道。
“阿斯尔,求你——”
“快着陆!”
希芬立刻向下俯冲,旋即飞过外墙,冲向庭院。它在一阵猛烈的颠簸中着陆,哀鸣起来。
“赶快!”阿斯尔低声说道。“解开你的皮带,我们赶紧走。”
“我不走。”
刀尖刺入皮肤的疼痛使她改变了主意。二人很快滑到地上,阿斯尔一脚踢中希芬的侧腹,这生物一下吸入空气,膨胀起来浮到空中。
透过被灯光点亮的修道院窗户,受到惊吓的人们试图看清庭院中的情况。有人大喊呼救。阿斯尔一个箭步冲到塔楼大门之前,将门拉开。如今不得不与阿斯尔“共患难”的女孩也只得与他一同跑向大门。在大门背后,是一小块楼梯平台,墙上的支架上插着的蜡烛火光摇曳。在蜡烛底下的地板上坐着的守卫惊讶地抬头望去,连忙去抓他身边带倒钩的长矛。阿斯尔用力一脚踢中他的太阳穴,随后便把瘫倒在地的守卫滚出门去。举着火把的人们正从庭院的另一端跑来,阿斯尔用力关上沉重的金属大门,并将门闩住。
塔楼的大门被拳头砸得砰砰作响。二人短暂地停下休整,玛拉恐惧地盯着阿斯尔。阿斯尔料想她一定会怒骂起来,但她只是靠在墙上,开始喘息。向下延伸的楼梯仿佛黑洞洞的大嘴,向他们打着哈欠——在那巨口之后,是石质的咽喉,直通火星的胃肠,那是名为大乔的怪物的国度。阿斯尔沉思着看了玛拉一眼,突然感到有些愧疚。
“我可以把你留在这里,”阿斯尔说,“但我得把你捆上。”
玛拉舔了舔嘴唇,先看了看向下延伸的台阶,又把目光转向大门——在门的另一边,守卫正在发疯似地大吼大叫。她摇了摇头。
“我和你一起下去。”
“我把你留在这里,牧师们会把你当作我的俘虏,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我和你一起下去。”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