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在中文语境中,“信念”(Belief)和“信仰”(Faith)似乎有着微妙的不同,但其实都和信任(Trust)有着部分相同的含义。当我们说一个人很有信念的时候,往往意指其人生的实践是内在自我坚定自信的体现。也就是说,他选择了某种“相信/确信”,并为之付出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选择相信基督中的“处女生育”,与你选择相信科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选择只是你人生中你认为的最优解。当然,对某事物坚定不移的置信会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你的知识框架逐渐推翻了你的确信。最优解的消失,使得你不得不再次面对人生的普遍质疑:确信是否本无必要?怀疑一切才是王道?可如果信念/确信退场了,我的精神世界该如何建构?有一桩关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轶事:当时他正在萨塞克斯郡的莱伊(Rye)拜访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这座村庄有点像是作家的静修所——H.G.威尔斯(H. G. Wells)、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和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都曾在那里住过。
那个周末,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住在亨利家旁边的旅馆里。当时已经60多岁的威廉对这位年轻作家充满了好奇,实在想要一窥其貌,于是他架起一架梯子,越过墙壁偷看。他的弟弟对此震惊不已——“谁也不会在这里干这种事!”他哀号道。那副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了威廉那永不停息的好奇心:他越过墙壁,只为窥见一眼对面的世界。
这则轶事是我在一本传记中读到的,题为《威廉·詹姆斯:在美国现代主义的漩涡中》(William James:In the Maelstrom of American Modernism),由罗伯特·D.理查森(Robert D. Richardson)所著。詹姆斯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但是在读过这本传记之后,我更爱上了詹姆斯的个性和人生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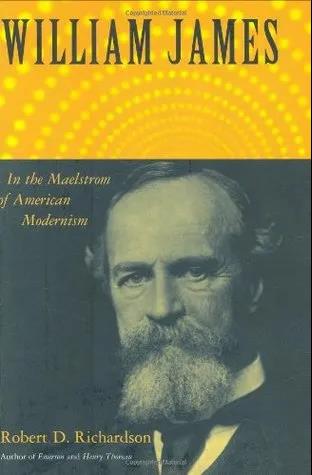
《威廉·詹姆斯:在美国现代主义的漩涡中》(William James:In the Maelstrom of American Modernism),罗伯特·D.理查森著。© Goodreads
尽管詹姆斯一生都有抑郁、失眠和神经紧张的倾向,他始终信奉乐观、希望、信念和活力的人生哲学。他坚持认为我们不是一片无意义的宇宙中的无助旁观者。我们是现实的共同创造者,拥有着自身并不完全掌握或使用的力量和能量。并且,不知何故,宇宙在乎我们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方式。
人到了四十岁后半,很容易变成脾气暴躁的中年人,这种时候,上面这条人生哲学便大有裨益,值得牢记在心。
威廉和弟弟亨利
威廉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宗教神视者(religious visionary),老亨利摒弃了制度性宗教,转而进行自己的宗教探索。威廉的弟弟亨利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家生涯,成名甚早,而威廉则是个反复无常、动荡不安的人。他先是接受了艺术家的培训,后来成为了医学生,随后又转而学习生理学,最终决定潜心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

威廉·詹姆斯(右)和弟弟亨利·詹姆斯。© ichi.pro在詹姆斯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因抑郁症抱有自杀倾向。原因之一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信奉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现实观,认为我们的思想是无助的奴隶,屈从于机械的、确定的过程。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对宇宙而言都无足轻重。我们是“动弹不得的旁观者”。
但是他设法重振了自己的生存意志,这多亏了两件事。
首先,他拒绝了唯物主义决定论,转而选择相信自由意志。他宣称:“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为应该是相信自由意志。”他认为,如果“意识”这种需要高密度能量的存在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进化过程还要费心留下它呢?
他开始建立属于他自己的有关意识功能的理论。他认定我们有一条“意识流”,而我们选择用自身的注意力来引导它。意识是有选择性的——它从一切涌向我们的嘈杂信息洪流中选出需要关注的东西。这种选择是由我们关心什么,我们认为什么重要来引导的。
随即,我们的注意力会牵引我们的情绪和行为。通过我们反复的选择和行动,我们创造出习惯,而从我们的习惯中,我们塑造出自己的世界。
他写道:
“我们感觉和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始终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通过慢慢地积累起次次的选择,像雕塑家那样,通过放弃特定材料的某些部分,而从那里脱颖而出的世界。另外的雕塑家,会让同一块石头中脱颖出另外的雕像!另外的心灵,从同样的混沌中,会感知到另外的世界!”改变他生活的第二件事是他结婚了。他犹豫不决,支吾其词,向他未婚妻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阐述为何她也许不应该嫁给一个古怪忧郁的单身哲学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做出了选择——一次信仰的飞跃,并且决定通过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去创造他们想要生活的世界。婚姻和家庭生活,加上他在哈佛的漫长职业生涯,给了他那不安分的灵魂一片港湾,让它得以出发去冒险。
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写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这本书成为了这门新兴学科里最成功的教科书,并帮助定义了学科本身。书中有许多有趣的看法,其中之一是詹姆斯对“什么是情绪?”这一问题的回答。
斯多葛学派/认知行为疗法(CBT)对此的答案是,情绪是认知判断。例如,我们看到有人对我们皱眉(A),我们用类似“她不喜欢我”(B)的看法来解释它,这种看法导致了情绪这一身体感受(C)。正如埃皮克提图(Epictetus)所说:“造成我们苦痛的不是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看法。”
詹姆斯颠覆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情绪不是认知判断,而是躯体反应。我们看到一头熊(A),我们的身体猛地开始行动,激活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C),随后当我们尖叫着逃跑时,我们的理性才追上进度,注意到“我很害怕”(B)。
哪一种观点是真的?都是真的。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调整情绪和治愈情绪困扰的有效方法。有时候,改换自身的信仰可以治愈我们——就像詹姆斯改换了他对自由意志的信仰一样。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身体调整我们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詹姆斯对用于情绪治疗的身体技巧很着迷,并写了一本名为《放松的福音》(The Gospel of Relaxation)的著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宗教、灵性、另类疗法和心理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宗教信仰和技术如何能够治愈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例如,他着迷于19世纪的医心和新思想运动【Mind Cure and New Thought movement,今天我们称之为吸引力法则(Law of Attraction)】,当时他目睹了这一运动席卷美国。它帮助人们放松他们的身体,开阔他们的心灵,并欢迎一股信念和希望的急流从……从哪里涌来?这可能来自他们的“潜意识”,也可能来自上帝。
也许说到底,这种能量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似乎起作用了:“医心运动传播开来,不仅仅是通过宣言和断言,而是因为其有显著的经验结果。”
这促使詹姆斯为自己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实用主义辩护作出了定义:要表现得像是宇宙关心你,那么你的信仰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提升人生的预言。
有时候,这听起来险些像是《秘密》(译者注:The Secret,著名心灵励志书籍)或《思考致富》(译者注:Think and Grow Rich,著名成功学书籍)的风格,而詹姆斯也的确为早期的新思想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应该说,早期运动不像后来的新思想运动那样具有粗俗的物质主义特征)。
但是詹姆斯的人生哲学与《秘密》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詹姆斯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你不能只是坐在你的房间里,想着积极的想法,然后期待着成功奇迹般地变成现实。我们的现实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共同创造的。其次,他从未富有远见地提出过“有毒的正能量”(译者注:toxic positivity,指无论何时何地,都过分及无效地强调快乐、乐观、积极的状态)。他对于邪恶、苦难和精神绝望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感受。
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宗教经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他像一个动物学家一样探讨宗教经验,像收容一园子神秘的野生动物一样收集许多不同的宗教经验描述,随即尝试将它们分类。
他定义的类型之一是“健全心灵的宗教”(healthy-minded religion),其典范就是像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或拿破仑·希尔(译者注:Napoleon Hill,《思考致富》作者)这样的人,他们总是看起来乐观开朗,从不觉得世界上有任何负面的事物。这让我想起了“礼拜日大会”(The Sunday Assembly)——我的朋友桑德森·琼斯就是这种“健全心灵宗教”的化身(译者注:Sanderson Jones,英国喜剧演员,“礼拜日大会”是他创立的无神论组织)。

桑德森·琼斯在非宗教人士的教会“礼拜日大会”上说:“生活是美好的,让我们庆祝它。”这之后又有“病态的灵魂”(sick soul),他有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感受:“我和宇宙都出了问题”。詹姆斯如此总结这种宗教态度:“救我呵!救我呵!”最后,当病态的灵魂跌落谷底时,他们放弃努力,屈服于某种更高力量的怜悯。随即,不可思议地,“拯救的恩典”似乎开始涌出。它可能来自上帝,也可能来自潜意识。我们无法分辨,但是我们可以评判这些“硕果”,并且说,宗教经验通常会使人更健康、更有活力、更富生机。
这个理论启发了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建立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威尔逊自己有过被宗教经验拯救的日子,后来他收到了一本《宗教经验种种》,这让他相信他可以为瘾君子们设立一个计划,鼓励他们“屈服于更高的力量”,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或者不相信上帝。很难说有多少人曾从无名会的十二步戒酒计划中收益——数亿人?
詹姆斯在《宗教经验种种》中的比较法——比较几种来自不同宗教传统和不属于任何宗教传统的人的个人描述,随即指出相似之处——激励了“心灵的而非宗教的”人群,这一人群时常坚称,所有这些不同的信仰和经历都指向一个终极现实(One Ultimate Reality)。

詹姆斯与他的朋友、哈佛大学的哲学家同事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进行辩论。显然,詹姆斯被抓拍的时候正在大叫“该死的绝对主义者!”与其说詹姆斯是长青主义者(译者注:perennialist,宗教哲学的一种观点,将世界上的各个宗教传统视为分享一个单一的、普世的真理),不如说他是多元主义者。每次你试图将人类的经验(包括神秘体验)放入一个系统中时,总会遗漏一些东西。就连詹姆斯的系统也自有其偏向——他忽略了所有的集体宗教体验。
因此,心理学或哲学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宗教体验是否指向单一上帝,指向一种核心的神秘体验?也许不是。为什么现实理应是“一”?也许存在多个神,多重的宇宙【是他创造了“多元宇宙”(multiverse)这个词】。也许宗教体验不是与最高统治者的联系,而仅仅是与比我们更高级的智能的联系。他写道:
“我本人绝不相信我们人类的经验就是宇宙里所存在的最高形式的经验;而是相信,我们和整个宇宙的关系,就正象我们的猫儿、狗儿和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一样。它们住在我们的客堂里、书房里,参加到我们的各种活动中来,但对这些活动的意义,却全然不懂……我们也就是万物的更广版的生活的切线。”当然……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也许我们最终对宇宙而言并不重要。不过话说回来,一条狗对它所居住的房子而言确实很重要!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太快给我们对现实的描述下定论。我们应该在认识上保持谦逊。詹姆斯总是同情那些例外的人、不合群的人、局外人、不被看好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许多朋友支持优生学时,他并不支持它。他对那些使用“堕落”等伪科学术语作为“棍棒”来打击他人的恶医持怀疑态度。
詹姆斯饱受抑郁症和恐慌症的折磨,他意识到疯子和健全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让他对病人产生了同情。事实上,他将自己收入的20%用于慈善事业,其中包括由他的朋友克利福德·比尔斯(Clifford Beers)发起的一项由病人主导的精神卫生保健改革倡议。比尔斯曾经被送入精神医院,并写下了他遭受虐待的经历。
詹姆斯最终相信了什么?他没有最终的信仰。生活是一种过程,一次旅程,一次探索,而他从不给出确定的、不再修改的叙述,或是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答案上。他总是对新的势力和思想持开放态度,谨防僵化成守旧的老顽固(他认为这种趋势通常在25岁左右开始出现)。
例如,他对他的朋友本杰明·布拉德(Benjamin Blood)的奇特念头就抱持开放的态度。布拉德写了一本关于笑气的书,名为《麻醉启示录》(The Anaesthetic Revelation),宣称自己曾通过笑气获得真正的宗教体验。詹姆斯亲自尝试了这种气体,随后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话:
“我们通常的、清醒的意识……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意识,而在它的周围,以最脆弱的屏障与它隔离开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潜在意识形式。”这些其他的意识状态——恍惚、遐想、梦境和狂喜——也有它们的适应性功能。詹姆斯宣称这一点,但大多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坚持认为,神秘体验是你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据。他在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09年,见了弗洛伊德和荣格,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有点生硬,但是他发现后者的年轻信徒(指荣格)与他更意气相投,尤其是在宗教经验的价值这一话题上。自然,在这个话题上,荣格此后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将会越来越大。
也许我们可以把詹姆斯的“过度信仰”定义为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我们的思想与某种“宇宙意识”相连。我们有意识的自我就像群岛中的岛屿,彼此之间有着潜在的联系,同时也与某种更高的仁慈力量相连。也许我们的灵魂能幸免于死亡,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此处,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努力付出我们最好的东西,充分利用我们尚未开发的能量和力量,并且表现得好像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宇宙很重要。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去海德公园散了个步,突然想起了成为基督徒的感觉(2013年,我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尝试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记得那种相信上帝存在的感觉:那是一个仁慈的、高位的力量,祂关心我,关心我如何生活。这给我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事实上,我的某些人生经历向我证实了这一信念。当我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厌倦和愤世嫉俗的时候,我就需要提醒自己这一点。
詹姆斯的哲学并不完美——它过于个人主义,而且有点过于接近《秘密》这类书籍了,令人不舒服。但是,它说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充满活力的事情:尝试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就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对宇宙(或上帝)而言很重要。我们无法确定事实是否果真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秉持着这一信念行动。
理查德森在传记的结尾明显地表达出了对詹姆斯的崇拜。“此人拥有无比炽热的精神!”他写道。他告诉我们,当詹姆斯结束《宗教经验种种》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时,爱丁堡大学的听众们突然自发地为他合唱了一首《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伙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我们所有人都这么说。
文/Jules Evans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julesevans.medium.com/william-james-on-living-life-as-if-it-mattered-52db7f18471b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