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前几天和母亲聊天,她说起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本来每年安排体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如果你是一位高血压患者,本来血压能够依赖药物维持在稳定水平,但一想到明天要起早去做体检反而血压就升高了……
这或许是心理原因导致生理变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群体性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或者说群体心因性症状的报道很多,且有很多从现代医学角度无法检测到病因(具体相似案例也可参看文末《文化束缚症候群是一种病吗?》)。正如文中所言,如果广义上的illness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话,那么文化、宗教、社群等因素自然也就无法忽略了。我们的大脑会跟我们开最恶劣的玩笑,它们总是试图解释、归类来自外界的刺激,有时会从身体和环境收集到的最微弱的信息中感知威胁。偶尔它们会过度活跃,引发最严重的疾病,比如幻觉、癫痫、瘫痪、昏迷,即便身体没有出现任何生理问题。
这便是爱尔兰神经学家苏珊娜·奥沙利文(Suzanne O’Sullivan)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领域。她居住在伦敦,专门诊治疑难杂症,比如患者出现癫痫发作现象,但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患有癫痫。她的任务是揭开公众对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illnesses,译者注:心身疾病指的是由心理社会因素引起,但以躯体症状表现为主的疾病)的误解。
比如,人们会认为心身疾病不严重,或者根本不是病,甚至是装出来的。奥沙利文会用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带领我们探究那些因解离症(dissociative disorders,译者注:解离症指的是在记忆、自我意识或认知的功能上的崩解,起因通常是极大的压力或极深的创伤)而不能生活自理的人。
奥沙利文和奥立佛·萨克斯(Oliver Sacks)一样都是极具天赋的作家,从她笔下的研究案例中,我们可以轻易体会到她对病人的同情。在她的新书《睡美人:以及其他神秘疾病》(The Sleeping Beauties: And Other Stories of Mystery Illness)中,奥沙利文走访了世界各地,调查了一系列奇怪而有趣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高度传染性。
在瑞典,一个女孩出现了无精打采的现象,其他数百个孩子也陷入了类似的昏迷状态。尼加拉瓜一位少年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可怕小个子男人,学校里其他几十个孩子也开始看到同样的鬼影。数十名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声称,他们都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疾病,比如头疼、疲劳和记忆衰退,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奥沙利文说,心身疾病远比我们想象中常见,但很少有人承认他们得了这种病。她解释说,实际上,“不接受诊断结果反而会加重病情,然后四处求医,不停地做测试,希望能够得到另一种诊断结果,即便这根本不是他们的真实病因。结果就是,你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
我在奥沙利文位于伦敦的家中采访了她,一起讨论了这些神秘的疾病以及医学诊断的问题。

心理和身体。苏珊娜·奥沙利文说:“我们不应该把身体和心理区分开。我们的身心是相互连接的。”孩子们沉睡的现象并非止于生理层面。“如你所见,这些孩子已经失去自理能力了。”© BBC
你提到过一种很奇怪的病,在瑞典,上百名儿童陷入昏迷,卧床不起。你去看望这些女孩时发现了什么?
我探访了两位小女孩,一个10岁一个11岁。10岁的小女孩陷入这种奇怪的昏迷状态已经一年半了,她的姐姐是6个月前开始出现的。当时的情景很令人震惊。当我们走进妹妹的房间时,她根本没有半点反应。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但当她的父亲想要把她扶起来时,她就像一个布娃娃一样柔软无力。不论出现什么动静,她都不会睁一下眼睛,而她过去一年半都是这个样子。她的父母用吸管给她喂流质食物以维持生命。
这被称作“放弃求生综合征(resignation syndrome)”。
这种现象刚出现时人们以为是小孩子变冷漠了,因为他们慢慢地对世界失去兴致,逐渐陷入一种完全无法交流的状态。这种疾病自21世纪初就在瑞典出现,一直到现在都有发生。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一些普通的孩子。患者都来自于在瑞典寻求庇护的家庭,当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瑞典时,就会出现放弃求生综合征。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来自生活特别艰难的小群体,比如雅兹迪人(Yazidi),他们可能是为了逃离故土某些可怕的事情才来到瑞典。但是我遇到的这两个孩子都是2岁就来到瑞典,现在已经10岁和11岁了,所以这种疾病肯定和她们在瑞典的生活有某些关联。

© BBC
你还见到了一直给她们看病的医生,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我和那位接待我的医生交流时,我希望能够谈一谈孩子们失去希望和出现症状之间的明显关联,但是她不是很乐意谈论这一话题。相反,她希望我这名神经学家能够推测一下这俩孩子大脑出现了什么问题。当然,我认为这是一次很有趣的对话,它能给我们很多关于动力和意识方面的启发,但却没有直击问题核心。孩子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她们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陷入昏迷,卧床不起呢?
我想先区分一下disease 和illness的含义(二者通常都被译为疾病,但disease和illness的含义稍有区别,后文的疾病都是指的illness。译者注)。当我们在说到disease时,它指的是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疾病,而不是我们对待自己身体的看法。而illness指的是我们感觉到生病,它受我们大脑中的期望影响。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自己是这些寻求庇护的儿童中的一员,并且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面临被驱逐出境时可能会对生活失去希望。当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些生理变化时,我们会作何反应?从疾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会受我们主观意识影响。想想要是你被驱逐出境会发生什么。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些不舒服,然后没有任何精神,接着你感觉自己起不了床,再接着你就会闭上眼睛。人们在有心思,遇到事情和压力状态下会出现身体症状,这一点并不稀奇。对这些孩子来说,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们的情况很极端。
另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不光只有一两个孩子出现这种症状,而是有好几百个孩子。它就像传染病一样,席卷了那些安顿在瑞典的家庭。
还是这个问题,这真的不寻常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义的疾病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当地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某些刺激因素会导致身体出现某些症状,而且你对此深信不疑,那么这些刺激就真的会很容易让你的身体崩溃,产生同样的症状。我们不应该把身体和心理区分开。我们的身心是相互连接的,如你所见,这些孩子已经失去自理能力了。
在你的案例研究中,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在其他地方,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喜欢听到他们得的是一种心身疾病。同样,在你的病人中,有人突然发病,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得了癫痫,但你认为,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心身疾病。
告诉我说自己得了癫痫并且经常发作的病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纯粹的心身疾病发作。这是身体对某种压力做出反应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它通常始于生理状况,比如昏厥。举个例子,一个年轻人上了一辆拥挤的火车,里面非常热,人们都晕倒了,这很正常。但是它会在人脑中埋下恐惧的种子,下一次再乘火车时,他会想,“希望这次我不会再晕倒了。”然后就会很不自然地检查自己身体,这样会导致症状加剧,最终发病。
你还调查了其他心身疾病,也都具有传染性。在尼加拉瓜,一些米斯基托人(Miskito)精神恍惚,产生可怕的幻觉,他们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种有趣的疾病,叫做“grisi siknis”(米斯基托语,类似于英文crazy sickness,有时也被译为“歇斯底里症”)。有些症状和医学诊断只存在于某些文化中。Grisi siknis就只存在于居住在米斯基托海岸的尼加拉瓜米斯基托部落。它主要影响青少年,尤其是女学生。患者会做出疯狂的行为,他们会狂躁地四处乱跑,然后倒在地上,癫痫发作。患者家属称,这种病太厉害了,需要好几个成年男子才能抓住女孩。它就像海浪一样在米斯基托族群里一波接一波出现。如果有一个学生得病,整个学校都会被感染。

© RTD Documentary米斯基托人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他们认为,得病的人是被一种叫做恶鬼(duende)的灵魂缠住了。患者经常会看到鬼魂,一个戴着帽子的小个子男人。他们认为是这个鬼魂缠上了病人,导致发病。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那些受到性威胁的年轻女性身上,她们经常受到年长男性不怀好意的关注。
米斯基托人是怎么应对grisi siknis的?
他们用传统仪式来对待它。当地的医治师会用草药浇在孩子身上。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方法很有效。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机制,当地人会用它来处理特定的社会问题。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女孩在某种压力下出现grisi sikni,这是她们表达痛苦,寻求帮助的方式,而不需要进行尴尬的对话,也不需要说明确切的问题是什么。

© RTD Documentary所以,进行这种听上去像驱魔一样的仪式,效果要比去医院看医生要好?
确实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在英美国家,如果有人出现了同样的发作现象,他们会去医院做脑部扫描和各种测试,但是治愈率只有30%。而米斯基托人治愈率是100%。这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开始接受宗教仪式,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应该问自己:这种疾病发作是想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
当米斯基托儿童生病时,整个族群的人都会聚齐起来帮助病人,而我们却会把发病的人隔离起来。我们可以从这种更加有同情心,且基于整个族群的应对措施中学习到东西。
在哈萨克斯坦,你还调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身疾病,你都有什么发现?
这场奇妙之旅发生在哈萨克斯坦中部的两个小城镇——卡拉奇(Kalachi)和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事情开始于2011年,当时一位中年女性正在摆摊儿,然后突然睡着了。其他货摊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把她叫醒。她被送去一家不错的医院,所有检测结果都正常。没有人能够解释发生了什么。一周后,她自己醒来,又恢复了正常。但不幸的是,这种现象传播开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133人陷入了神秘的睡眠,一些人还出现了各种其他症状,比如幻觉。哈萨克斯坦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试图找出原因。他们采集了头发样本、大气样本和水样本,期望能找到毒药或者其他任何能解释这一切的东西。
附近有一个矿井,所以他们有可能是中毒了。
那里曾经是一个采矿小镇,这些人在铀矿里工作生活多年,从未生病。这个铀矿自20世纪90年代就关闭了,过了20年他们才生病。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调查矿井是否有毒,只是这些检测十分详尽细致,却什么都没发现。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城镇的照片时,我认为这里十分贫穷。整个城镇残破不堪,建筑摇摇欲坠,人们没有工作。我一开始和许多医生一样,猜测这些人是因为压力太大导致精神分裂,然后陷入昏迷。但当我到了那里,我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
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被运送到这个秘密铀矿,他们称这里是天堂,一开始我根本不能理解。但当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后,我意识到,这里曾经确实是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天堂。这里受到莫斯科的照顾,有电影院和一家大医院,商店里摆满了商品,这些在哈萨克斯坦其他地方是根本买不到的。但后来,一切都变了。铀矿关闭,他们的生活从受到特别优待变为十分艰难。
人们在遇到事情和压力状态下会出现身体症状,这一点并不稀奇。

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卡拉奇。© RT因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就不再支持哈萨克斯坦这些城镇了。
铀矿关闭了,这个小镇失去了保护。但这时候居民还没有生病。你原本以为有人会因为压力生病,但他们却挺过了这些困难时期。问题发生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因为政府关闭了大量娱乐场所,人们的生活少了很多乐趣。镇上只剩300人,而且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因此,政府希望将他们让他们搬到一个更大的镇上,但人们并不想搬家。
当他们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搬离自己的城镇。这就好像一个爱情故事。小镇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和安慰,他们愿意在这里守候到它重新焕发活力的那一天,但也意识到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昏睡症是作为一种复杂的问题解决方案出现的。当离开城镇并重新安顿之后,这些人就康复了。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城镇,是昏睡症帮他们做了选择。
这些患者相信他们是因为铀矿中毒,他们不希望听到这种心身疾病诊断。
当地居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物质,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坚信他们是中毒了,因此才会离开小镇。这也能理解。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心身疾病的人很脆弱,或者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骗子,既然这样的话,谁还会承认自己得了这种病呢?

© Mysterious Facts当你和有过昏睡症的人谈话时,我想你应该说过他们并没有中毒。你们之间应该很难沟通吧。
关于这一点,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我相信一种西方医学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我能向人们解释他们生理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是一种心身疾病,他们就会相信我,并得到释怀。但事实情况完全相反。这里的人只相信他们自己的解释。当你试图提出心身疾病这个话题时,无论你有多委婉,他们都不想听。现在我明白了,或许有时不提这件事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心身疾病本身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那么或许试图把它公之于众是不明智的。
让人们相信错误的诊断,这可不像是一名西方神经学家的回答。
我不是鼓励人们相信我自己都不信的诊断,但我试图多听别人是怎么讲的,这样我才能了解问题在哪儿。西方医生经常会跟病人起争执。我说,这是心身疾病,病人说,“不,这不是。”这样的争执很没有意义,双方都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对我来说,向病人解释心身疾病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时我也会更多地倾听他们自己的故事。有时,心身疾病是一种具体化的叙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我需要去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出现的现象的。显然,合理是有限度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案例都是那些失去家园,或者相信灵魂附身的人。但你也写到,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出现了一系列症状,比如头昏、头痛、记忆问题、疲劳等,也就是所谓的“哈瓦那综合征(Havana Syndrome)”。有很多报道称,一定是敌人对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们使用了秘密武器。但是你不这么认为,是吗?
不仅仅是我不相信,这些报道的说法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可能,不过是坊间传闻,就像相信你被鬼魂附身了一样。声波武器攻击的假设没什么说服力。2016年12月,一名驻古巴的美国外交官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同时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症状,包括头痛、头晕、站不稳、很难注意力集中等。于是就有谣言称,大使馆的人受到了声波武器的攻击。

© Breezy Scroll也有可能是某种微波能量武器。
嗯,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很有趣。一开始人们认为是一种声音武器,因为有人听到了声音。接着其他人也说他们在听到了声音后生病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医学问题——声音不会损伤大脑。异常响亮的声音可以通过耳朵损伤听力,但在不会损伤大脑。科学家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他们说,“它或许不是听觉范围内的声波武器,或许是某种超出听力范围的东西,比如微波武器。”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认为有声波武器的前提是人们听到了声音,那么现在又认为是微波武器的假设就不合逻辑了,因为人们听不见微波武器。而且,还有许多生物学原因解释为什么微波武器不可能——这种武器根本不存在。我不是一名武器专家,但我是一名医学博士,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微波武器攻击,那么微波武器肯定不止针对大脑。如果一种微波能量从远距离直接射向一个人,那不可能只损伤大脑。他们的肾脏、心脏还有肺部为什么没有出现血管问题呢?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微波武器这个说法一直存在,直到现在媒体都还有报道。
这不仅仅是我不相信,这些报道的说法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可能,不过是坊间传闻。
美国政府派了一些顶尖的医生去调查,他们认为可能是某些秘密武器导致了这些症状。
是的,媒体关于报告内容的报道,以及报告内容本身之间的差距十分有意思。史蒂夫(Steve,本文作者),你读过那份报告吗?
没有。
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我读过报告,而大部分人都没有。报告称,接受检查的人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他们甚至都不能确定这些人遇到了相同的事情。最后,他们排除了很大一部分报告自己受到这次攻击影响的人,而把重点放在更少的一部分人身上。然后,他们排除了心身疾病这一解释,而且没有说明为什么。接着又给出了很多心身疾病相关的诊断,但却用委婉的说法掩盖了事实。比如,他们会用“功能性的”这样的词,但是后面加了括号,写上“功能性的,不是精神性的”,这是医生委婉给出心身疾病诊断的一个办法。他们确实提到了认为是微波能量,但是当你读完整个报告,你会惊讶地发现,相关证据少之又少。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相关人员。
那么你认为美国驻古巴外交官遭遇了什么呢?
我们无从得知第一个人发生了什么,因为在这种突发情况下,第一个人得的病可能和其他人完全不同。但是他会定下后面事情的基调。当你了解使馆人员的经历时,你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他们被告知,当时有可能被声波武器攻击,因此,如果再听到奇怪的声音时,他们要躲在墙后。他们还需要不停地开会、检查身体,如果有任何症状都要看医生。当人们被要求检查自己身体时,焦虑情绪就会不断升级。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50年的紧张态势之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才刚刚开放,人们担心,古巴人会在大楼内安装窃听设备,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紧张。
这些人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受到威胁,因为有很多先例表明,驻古巴和俄罗斯大使身上会被安装窃听设备。而且他们又被告知,攻击随时有可能发生,并且要检查身体。试想一下,当你检查身体看有无异常时会发生什么?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出现了问题。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感染了疾病或者受到攻击,请检查身体,”你会立马发现那些平时你注意不到的刺痛和不适。
但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古巴。美国驻中和德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也报告了类似症状。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全球,伦敦、德国都出现了病例。但这就是传染性症状的特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驻古巴外交官是如何得知他们有可能得了心身疾病的。参与事件的医生表示,这些外交官不是在演戏或装病,他们不想生病。
现在,如果这是你对心身疾病的看法,你无异于在对你的病人说,“好吧,这是你的选择,你要么是在装病、疯了、想要生病,或者你是被声波武器攻击了。”你会选择哪一个解释?答案显而易见。
文/Steve Paulson
译/Rachel
校对/boomchacha
原文/nautil.us/issue/107/the-edge/the-neurologist-who-diagnoses-psychosomatics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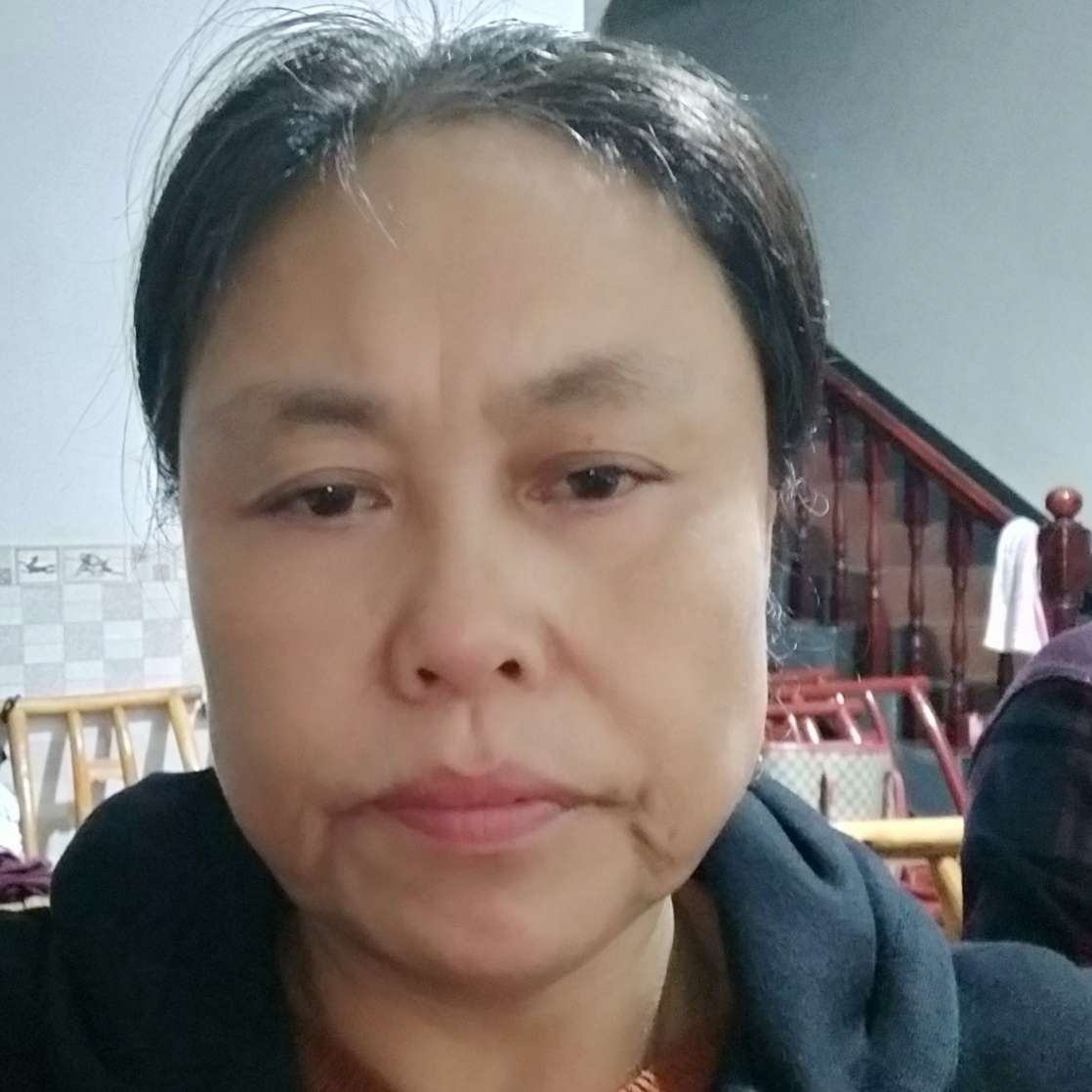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