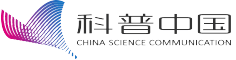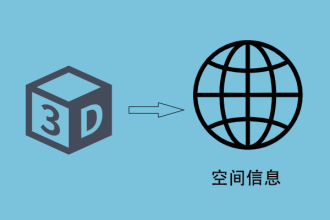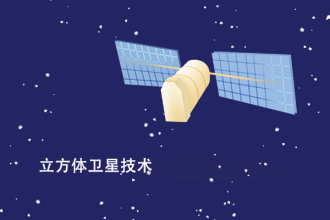匹诺曹的木偶剧科普中国-科普文创 2017-12-18 |
一、
“你对韩雨的死了解多少?”你问我。
一年多以前,4月1日,一位客人造访了公司。半小时后,你们发现了办公室里死去的韩雨。此时访客已离去。这起案件被定性为反测谎组织的报复。
“我只知道媒体报道的这些。”
实际上不止,但我不想说真话。
“不会是报复。”你说。
我同意。要是报复,目标就应该是你。
“当时的来访记录和监控数据都没有留下来,只有安保系统的最高权限才能进行删除操作,不然就是被黑了。警察也没有头绪。”
“过了这么久,你又关心起老韩了。”我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嘲讽。
“以前我觉得找不到真相,现在不一样了。”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我已经看见了实验台上的东西。两周前,是我跟你一起把它封起来的。
“曹远,你能帮我吗?”
这话似曾相识,我和老韩第一次碰上你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二、
“你们能帮我吗?”
高中社团文化节的最后一小时,你突然跑来扯住了老韩的袖子。
费了一番功夫,我们才弄明白你从别人那听说了我们的摊位。“信息科技社搞出了能读心的程序。”而这正是你要的。
我猜你没听完他们的说明,那个程序是这么运作的:体验者心中默想学校里的一个人,然后回答给出的问题,最多十五个是非题后,程序会猜出这个人。
这当然不是读心,这只是用扒来的代码和学生数据生成的决策树。
而你要的是一个能判断出别人说的是不是谎言的东西,一台测谎仪。原因很幼稚:你怀疑舍友的男友对她不忠。你希望这台机器输入简单,最好是只有话筒和摄像头,这样就不需要往那个男人身上绑血压仪和脑波仪。你还希望它的错误率至少在百分之一以下,这样不至于发生误会。而且你不明白这些要求多荒谬。
我对你的印象至今没变——无知、轻信、感情用事。
但老韩才是社长,而他从没被校花扯过袖管。
于是我们查找文献,尝试不同的算法,像嫁接植株一般嫁接它们,像挑选果实一样挑选它们。数次迭代后,它们被采集、发酵、蒸馏,全新的酒液被装进全新的瓶子。
我们做出了你要的机器,它又反过来改变了我们。
三、
说到底,它对老韩的改变是最大的。站在老韩的墓前时,这个冷笑话般的想法跳进我的脑海。如果老韩还活着多半会被逗乐,他笑点一直都不高。然后我听见脚步声,看到了你。
“昨天的新闻还说你在芝加哥。”我说,看来媒体的嗅觉终究有限。
“最近怎么样?”你问。
“还行,最近不用去看心理医生了。你倒一点也没变。”换句话说,还是让我反感。
“虽然这个场合不一定对,我想和你谈件工作。曹远,我们从韩雨留下的东西里找到了一些资料。你想回来解读它吗?”
“他都过世一年了。”
“我们已经尝试了一年,但还是不行。”
“我好几年没写代码了,为什么觉得我能懂?”
你沉默,然后我品出了其中含义:“你们还在开发那个测谎系统。”
“不再针对民用了,现在我们的对象是……”
“某国政府,还是军方?”
你沉默。
“那就是都有,不止一家。那你现在也算半个军火商了。”我嘲讽。
“真相对于一般民众只是奢侈品,信息对大人物才有价值。你以前说的。”
“现在你终于认同了,”我笑起来,“说说待遇吧。”
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接了一份工作,但这是句谎言。
四、
老韩留下的东西并不太复杂,但让人费解。
例如,资料中的这一部分看上去像是某种训练后的神经网络,但我却把握不住它复杂结构背后的轮廓;眼下的这组参数或许则是权重矩阵,可我仍看不到它的任何实际意义。
“什么是权重矩阵?”本突然开口问。
我没想到如何用英语准确地解释:“就是一组代表重要度的……东西,用来描述输入到解之间的对应关系。”
如果你是程序员,那你大概听过或试过这一套:当发现不了代码里的问题时,找一只橡皮小黄鸭,仔细地向它解释那些代码,最终问题就会浮现。本现在就是我的小黄鸭。
起初,公司要建立一个团队,我表示自己不会与其他程序员合作。这句话被误解成我需要不会编程的下属。然后这个法国青年来了。
本对生活满怀热情,每周都会参加市民话剧团的排练,他喜欢讲笑话,但每次讲到一半自己就先笑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安排的,他有些像老韩。
他对我很好奇,起初是因为董事长(也就是你)常来探访,后来他又不知从哪听说了四年前的事。我看得出他对此有许多疑惑,但又担心向我提问会造成不必要的冒犯。
那天晚上,我终于解开了问题的关键。于是我关上电脑,转身对本说:“问吧,什么都可以。”
迟疑了一小会后,他开口:“你当年早就知道贩售面向普通人的测谎系统是个坏主意了?你预料到了后来那些混乱吗,比如……那些反测谎极端组织?”
“那些组织中的一个就是我创立的。”我说,而他险些当真。
“这只是个玩笑。你看,我反对那个项目,只因为我就是个常说谎的人。”
如果失去谎言,人们会用真相来填补空缺吗?或许会,但他们往往更愿意使用某些更糟的东西。事实证明我没说错。如果你不是那么固执,我们本来可以避免那些惨剧。
“你是对的,谁还能不说谎呢?”本耸耸肩,“不过这话可不能让小孩听到。曹,你有妻子或孩子吗?”
“没有。”
本从口袋里递过来两张票,上面写着“木偶奇遇记”。
“那就和朋友去看吧。我们的剧团下个月要演出了,在市民剧场。我是主角。”本说。
五、
“‘匹诺曹’?”
你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实验台上的仪器。它有些简陋,没有机壳,杂乱的导线将几块板件联为一体,上方是一枚指示灯。这是我们过去的第一台样机,它也叫“匹诺曹”。
“老韩的参数是为它准备的。你还记得它指示灯的含义吗?”
“绿色是真话,红色是谎话,黄色表示无法确认。”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实验室被一堵带玻璃窗的隔墙一分为二,被试者与研究人员分属两侧。只有用话筒才能向对侧传话,这保证被试者不会听见研究人员的讨论。
“这位是我们的志愿者。”我指着坐在隔墙另一侧的本说。
两台高速摄像机与一只话筒正对准着他。
我打开话筒,用英语下达指示:“我们会不断提出是非形式的问题,你只需给出肯定回答,例如‘是’或直接点头。”
本点头。
我提问:“你的名字是本·罗切尔吗?”
他说:“是。”指示灯变成了绿色。
“下一个问题,你认为地球是平坦的圆盘吗?”
本点头。指示灯变成了红色。
“你也问一个,随便什么。”我将话筒让给你。
“质数有无限个吗?”你问。
“是。”指示灯又一次变成绿色。
“这有什么意义吗?”关上话筒后,你问我。
“我会解释的。接下来我们试着用法语和汉语提问。”
我们使用不同语言测试同样的问题,测谎仪每次都做出了正确判断。问题换成别的,然后是类似的环节再次重复。
“它和原本的‘匹诺曹’区别在哪?正确率吗?”
“关键不在这。”
“那在于什么?”
“语言,”我说,然后开始幸灾乐祸你的困惑,“他不懂汉语,”但测谎仪工作了。在被试者本人并不理解自己被问了什么的情况下,它正常工作了。”
你脸上仍是不解,你毕竟不是老韩。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断言,“仪器捕捉的是人们说谎时的不可控生理反应,如果他意识不到自己在说谎,又怎么会触发仪器?”
“原因不明,可事实如此。老韩没留下能参考的其他信息。”
你犹豫片刻,再次开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尽管被试者自己没意识到,但在潜意识里,他听得懂汉语?然后系统识别出了那些由潜意识引发的反应?”
“总之,有什么触发了系统。潜意识——先不论准确与否,姑且就用它来称呼那个触发源——想知道所谓的潜意识对世界了解有多少吗?”
在向你演示前,我已经对十数位志愿者进行了上百轮测试,结果都是一致的。
理应有结论的客观问题都能被回答。任何你认为只有自己会知道的,你认为不可能有人知道的问题。
无论提问的语言是否是被试者所理解的语言,也无所谓这些问题是来自被试者不掌握的知识、陌生人的隐私、失传的历史文献,或是人类尚未解决的猜想,
本离开后,我们开始正式讨论。
“你想告诉我,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藏着另一个无比智慧的意识。”
“它未必在大脑里——甚至未必是一种意识。”我纠正,“至少可能不是那种具有人格的意识。”
“为什么不是?”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它不对我们说谎呢?”
“或许是因为只有我们才需要谎言。”你表情苦涩,这倒是我所乐见的。
六、
我还记得四年前的你在内部会议上的总结:“人们不需要谎言。我们要销售的是测谎系统,也是他们知晓真相的权利。”
“如今你不信人人有权知晓真相的那一套了?”我问。
你只是垂下视线。
“那好,董事长,做决定吧。这已经不是测谎仪——每个是非问题的解答、我们所有认知的极限、或许还有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答案,大概都在这了。你要将它交给你的雇主吗?”
他们不会在乎生命和宇宙,他们只会在乎更实际的东西,比如某艘核潜艇的位置。
你终于做出决定:“实验室、机器、资料,全部封存吧。”
这结论足以让那些信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老学究们晕厥一万次,但这才是对的。
“我不想看着一切变得更糟。”你说。
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我知道一切仍会变得更糟,只不过在此刻稍稍放慢步伐。
七、
现在你又后悔了。
“我想知道老韩死去的真相,这是最后一次。”
“那好吧。”我说。
老韩不拒绝你的请求是因为喜欢你。而这一次,我只是乐于看到飞蛾扑火,老马走向悬崖,伊卡洛斯最终陨落,蜡质羽翼融化成泪水。
我坐到了隔间里,你把“匹诺曹”放到了我能看到的位置。
你打开话筒,提问:“你知道一年前的4月1日,探访韩雨的那个人吗?”
问话的对象不是我,是另一个存在。
我点头。指示灯亮起绿色。
“他是男人吗?”
点头。绿色。
“是外国人吗?”
点头。红色。
事情就这么进行着,或许这也算一棵决策树。
再有十多个提问,你就会得到答案。
不过事情可以更简单。
于是我拿起话筒,告诉你:“别浪费时间了,那个访客是我。”
绿色。
“我去了那里,看见了老韩的尸体,离开了,仅此而已。”
绿色。
“你为什么……去那?”
“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我没杀他。”
绿色。
“那……你知道是谁杀了韩雨吗?”
“我知道。
“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老韩的研究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做了和现在差不多的事。我知道。
“他是自杀。他有能回答一切的机器,如果想破解安保,那是很容易的。
“陆晓诺,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选择了自杀,你一无所知。”
指示灯仍是绿色。这次你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这让我有种幸灾乐祸的满足。
八、
“还记得我最开始找你俩时用的理由吗?”
木舞台剧的第一幕刚结束,老木匠沉沉睡去,一旁坐着的是本扮演的匹诺曹。帷幕渐渐拉上,你就在这时突然开口。
“抱歉,我早就在说谎了,那个对舍友不忠的男友不存在。”
“其实是你的男友?”
“其实是我父亲。”你语气平静,倒更像在谈论舍友的事。
“我们也有事瞒着你。测谎系统需要训练集,于是那时候老韩自告奋勇去黑了十多家大学研究所和医院的心理数据库。”
你轻笑起来,笑得像曾经的老韩。
“告诉我他自杀的原因。”你说,“你一定用‘匹诺曹’确认过。”
我依稀能听见从帷幕背后传来的,工作人员搬动道具的声音。
“和我过去一样,”我说,“抑郁症。天天与谎言为伍不是什么快乐的事。”
“他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
“越是这样的,越容易想不开。”
你没再接话。
大幕再次拉开。仙女登场,挥动魔棒,匹诺曹缓缓站起身。
九、
走出剧院,你和我挥手作别,带走了我的谎言。
我不会为此道歉,你本来就不配知道事实。
有一个连侦探小说的读者都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发现某个秘密后不久就死去了,那他的死不大可能单纯,即使是自杀。
韩雨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从剧院到公寓有条近道,我拐进小巷,不出所料,戴面具的身影出现了。
“我想请问一下,”我思索如何用英语向对方传达我的意思,“本,不会汉语而且不用化名的间谍在你们那常见吗?”
“这算为了防止被测谎而做的安排。”
我有些后悔,前些日子要是多问一句“你是不是间谍”就好了。
“你知道我们要什么。”戴面具的本举起带消音器的枪。
“迟了,机器和资料都已经销毁了。”
“你的脑子还记得。至于那些‘资料’,我们有。”
你这句话是最后一块拼图。
“你们意识到了韩雨的发现,而他不愿意合作,但你们有太多方法撬开一般人的嘴,于是他只能删掉数据,用自杀封自己的口。”
“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合作,还付出了很多资金,而你们却试图藏起应有的回报。”
“没有我,是他们。”我纠正,然后继续,“你们只能反过来,把过去收集到的那些情报碎片伪装成韩雨的资料,留在现场。”
“然后等着你来解读。”
“把我骗去那的也是你们。”我补充。
“那张记忆卡就在办公桌上,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也有一份。可你就那么默不作声地走了。这让一切晚来了一年。”
一切仍会变得更糟,只不过在此刻稍稍放慢步伐。
“我怕事,我毕竟不是侦探。”
“现在呢,怕事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吗?”
我摇头,本露出近似于同情的笑:“就像你说过的,我们会有很多方法撬开你的嘴。”他的枪对准了我的小腿。
然后枪声响起,不止一次。直到他高大的身躯彻底平行于地面,本还在盯着自己尚未扣动扳机的手。
“就像我说过的,”我俯视着他,“那些组织中,有一个是属于我的。”
巷子角落出现的同志们向我点头致意,他们开始收拾现场。我拾起落在地上的面具,它很精巧,几乎不影响佩戴者的视线。
这倒挺适合我的。
如果老韩还在,他或许也会这么想。
责任编辑:科普云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