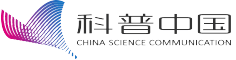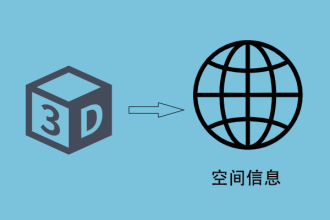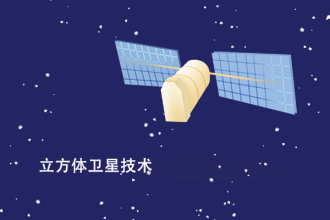我大口呼吸着,耸高双肩压低出气的声音。嘘,别被人发现了。装模作样用脏兮兮的左边袖口擦了下右手端的稀粥,左手顺势一滑将左碗里的粥呈了点到右边碗里。盛粥太太叮嘱的话还在耳边:“奥利尔,你小子记得把这碗给汤姆,他去方便一下,你偷喝他可不打死你!”
我奥利尔长得瘦小不过这灵活的手上功夫可不是吹的,得意地伸了伸舌头,坐到屋子最边缘的凳子上开始喝今天这仅有的一顿稀粥——脱脂稀牛奶加燕麦。
干涩的嘴还没接触到碗,一个大力袭向腹部。翻身栽下椅子,很争气的,我在摔倒前不忘把碗稳稳地放到了桌上,一点粥没洒。
面前一个膀大腰圆的少年涨红了脸,猛踢了我一脚,指了指两碗看起来分量确有不同的粥:“你敢说你没偷喝老子的?奥利尔你他妈在放屁!”周围人勾着身子喝粥,他这一霹雳着实大,连精神失常的画画老头都移了下呆滞的眼神,不过很快又低下他那长满脓疮的丑陋脸庞。
救济院屋里的很多个喉头上下滑动,喉头的主人表情空洞,劳动的时候他们就想着喝粥,喝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想。
他们在等死,我知道。
我抿起嘴盯着愤怒的汤姆,暗中咽了把口水,斩钉截铁道:“我没有!盛粥太太又不能把碗盛的一般多,我随意挑了一碗哪知道它就多咯?”
他被我逼急,呲着牙:“滚,这两碗都归老子!”
妈的,我心里呸了一口。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待在救济院十五年就被欺负了十五年,也真够窝囊的。心一横,一个旋身我抓起两碗粥,在汤姆震惊的目光里,咕噜咕噜吞完了。我对着他把空碗摇了摇,瞟到他颤抖的赘肉,我狡黠地笑,靠,真爽。
意料之中的几个大巴掌扇了过来,我扑倒在桌子跟前,他扯住我胳膊玩命踢我肚子,“老子不信你不把粥吐出来!”
不好,我一哆嗦,只好蜷起身子紧闭嘴巴,生怕好不容易搞到的食物吐了出来,连饱死鬼都做不成也真是窝囊。顺便用桌子跟蹭了下鼻血,然后哑声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干嘛去了,女集中屋的老淫妇,跟多少男人睡过,哈,你还下的去手,哈哈哈哈。”我咧嘴笑,我此刻的嘴脸一定又可恶又恐怖,我很满意他的愤怒,这愤怒砸在我头上、腿上、腹部,痛并畅快。
他骂我是条狗,他吼着要把我打死,要看着我死,要把我丢到谷地的深处去,他尖利地叫,我不明白他为何有这么多怨恨,为什么会希望别人到那样的境地呢?
这里有很多人,管理者、工作者、被救济者……他们都不会在意一个穷小子会不会被打死,可能被打死更顺从民意,因为少了张嘴,或者他们以后能分到的粥会多那么一滴。救济院建立之初,牧师给立法者写了一封信:“救济院应该是一个充满痛苦,伙食糟糕,充斥堕落和屈辱的地方,应该是一个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地方。”
政府和贵族指责穷人的贫穷,谷地正在大建设中,是有多懒惰多肮脏的人才会沦落到救济院呢?只有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境地才会去救济院。
血糊住了眼睛,嗒,嗒,嗒,嗒,我听见人们离开屋子的脚步声,他们还要为了明天的这一顿饭而劳动。我看战争、死亡、老头画中的魔鬼,就像看汤姆,看别的人一样,到处渗透、侵略、扩张,他们的触角在一切之中,我的不眠之夜,我的肉体,我的灵魂。
眼前越发黯淡,打在身上沉闷的重击声渐远了,饥饿的人们有时会偷偷割下死人的生肉填肚子,我会被割哪里呢?我肉不多,估计只剩下红色神经贴着的骨头。那一定顶恐怖的,不过现在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神呀,原谅我的卑微吧。人在软弱的时候果然需要安慰,我忽然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开始企盼往生。若有来生,若有来生……不,哪里会有神呢?神哪里能容忍这种污秽的地方存在呢?
腐朽黑暗的气息堵了我的五感,可是忽然有一点光,吱呀吱呀声音放大,然后越来越亮,眼皮撑开了血渍,我看见了一盏煤油灯摇摇晃晃而来,沿着回环往复的雕刻藤曼向上,是一只修长的手,中指扣着一枚回形的戒指。
有指针咔咔地走,听得那个男声清淡有礼:
“在下埃拉,求见奥利尔阁下。”
我一向扛打,醒来之时全身还是碎骨般疼痛。从未走出过救济院暗红色颓败的围墙,可是眼前置着精致的玻璃杯,杯口银制羽毛托着一块方糖,对面人胸口的衬衣褶皱离得桌台恰当的距离,他眼睛好像很不好,正眯着眼睛吃力地往杯口掺水。
这是——“酒馆”?
水将方糖融化溢落到杯腹,绿色的液体泛起团团悬乳,对面人对我略略欠身,盛了小杯液体递我。
“请您尝尝苦艾酒。抱歉,忘了自我介绍,很荣幸见到您,在下埃拉。”他不过二十来岁,穿着考究的服装,英俊的脸上是彬彬有礼的笑容。
“奥,奥利尔。”我迷迷糊糊说着并端杯饮了一口,奇怪的味道差点没让我吐出来。
埃拉用食指和拇指拈住杯,很是痴迷地欣赏着浑浊与清透交替,一饮而尽。看出我的不适,他微仰头:“来杯威士忌。”几杯琥珀色威士忌很快被端上来,他转向我,道:“不喝过苦艾酒,你又怎么知道威士忌的甘醇?”
埃拉带着我品酒,跟我讲了很多我从未听过的趣事。他说刚出门的那个杵着拐杖的男子其实是个最卑微的异能者。异能者和咒术师被普通人类管控的社会视为异类,被驱使去做最危险的探索,这人在谷地最底层劳动了四十年。他的特异之处不过是小腿三百六十度旋转。有个军官来底层视察,觉得他这点有趣,就派人剜了男子两块膝盖骨,看他小腿还能不能旋转。遗憾的是那小腿就直楞楞吊那儿了,军官扫兴地赐了他离开底层的权利,作为对他的补偿。
他又说远处窗边那个戴十字架的从前是个主教。阅遍神书断定世界的年龄是四千六百岁,神在起源之时创造了人类。为此他受到民众敬仰。可是最近一队科学家在谷地深处发现的化石经鉴定至少有上万年历史。牧师不相信,他亲自看完那化石,一路狂笑着回来。后来,他在祈祷主持前都会喝很多酒,有一天他终于被赶出了教会,他倒在阶梯上,双手把十字架举过头顶,看见谁都问:“我们死后是什么样子?我们死后是什么样子……”
他最后说左边那个戴高帽的老头子年轻时却是个开纺纱厂暴富的中产阶级。老头是个虔诚的信徒,却喜欢炫耀财产,家里大厅摆了188幅油画和,72座雕塑,132只椅子。他有一个太太,一个女儿,却有四个佣人——厨师,客厅侍女,男仆和女仆。某一年这个富商莫名爱上了绘画。起初他只是请太太、佣人扮演模特,后来他开始请一些陌生女人作模特。富商变得越发大胆,专挑着太太出门的时间找模特,他让女人们褪去衣裳,赤身裸体站在他面前,他抚摸她们的肉体,赞颂是神赐的光明。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这时候那个老头已经离开了。
“其实这些女人不是穷人就是妓女,他和她们上了床,不知道通过谁感染了梅毒,还传染给了他太太,和他刚出世的孩子。那可怜的孩子流脓而死,死的时候裹布上全是黑黄的黏液。太太拉了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那富商变卖了家产,想乘灯塔和女儿一起向上回到地面,远离谷地里流言蜚语,可是他女儿在一天夜里偷了他所有财产抛下他一个人,乘灯塔离开了……”
埃拉微皱眉头讲完最后一个故事,放下早就见底的酒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那些都离我很远,可是他说的时候却有种魔力,让我觉得就是方才发生的事。他把黑礼服露出的白色衬衫袖口叠得整齐,掏出怀表看了眼,站起来说:“我们出去转转吧。”(节选)
该作品为第六届“光年奖”原创科幻小说大赛参赛作品。想了解更多,请点击:
http://club.kedo.go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85
“光年奖”由蝌蚪五线谱网主办,旨在提供科幻竞技平台,发掘科幻新作家,提升人们对科幻的关注。比赛通过在线征集、公众投票、权威点评等方式评选和推荐优秀科幻作品。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