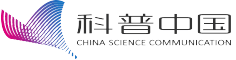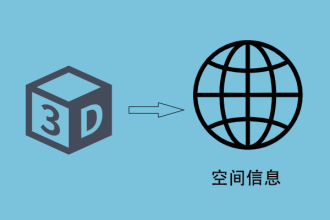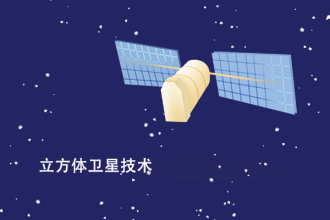做环境毒理学挺焦虑的:做不出毒性,愁论文,做出毒性,又替地球担心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 2021-01-21 |
我怎么给蚯蚓染毒?打个比方,就像在饭桌上给人灌酒。
作为环境毒理学家真的非常烦恼:做不出毒性,焦虑发不了文章;做出毒性后,又很替地球担心。
2020年9月20日,“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第26期“烦恼的环境er”演讲现场,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王雯带来演讲:《蹂躏完一代代实验动物,我意识到这是一门找茬的科学》。
以下为王雯演讲实录:
2020.9.20 天津
大家好,我是王雯,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安全工程学院,研究方向是环境毒理学。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的研究方向,我注意到现场环境稍微安静了一下——大家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如果是在私人场合比如家庭聚会时,大家听完我的研究方向,可能下一眼就会望向我的家属,眼神意味深长。
因为受到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影响,很多人对我们专业的误解很深。所以,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不是环境毒理学?或者说,我们不是干什么的?
左边这张图,是我们实验室的危险化学品药品柜,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钥匙孔,对应的两把钥匙,一把在我手里,另一把在我同事手里。也就是说,里面的药品需要我们两个人同时开锁才能拿到,基本上和传说中普京提的手提箱是一个安全级别。
有些化学品之所以被称之为“危化品”,一方面,因为它可能具有毒性,比方说做实验时如果防护措施没有做到位,可能会起些皮疹或者呼吸系统受刺激而流泪,此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具有易燃易爆易制毒的特性。
不过,即便我真的拿到这些药品,要出现一些预想中的毒性作用,也并不容易。

给大家举个例子。上图是不同种类的可乐含糖量,像蔗糖这种非常优秀的甜味剂,也需要加这么多才能达到大家期待的那种甜味效果。
同样,如果我们想要化学品表出毒性,也需要很大剂量。所以,我觉得投毒这件事,难点不在于能不能把化学药品从药品柜里取出来,而在于怎样劝人把它喝下去——这可能是个心理学问题。
即便突破了伦理学、法律、心理学等等各种屏障,真的走到最后一步,你还是会发现,投毒这件事真的做不了,因为毒理学日常实验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
首先,生物实验误差非常大,并不是每一次使用相同剂量都会达到同样的预想效果。
其次,我们做实验用的都是实验动物,某种化学品对某种实验动物的毒性效应不能直接外推于人。因为物种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差异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不能拿动物实验的剂量直接用来给人类做实验。
第三,生物本身的个体差异很大。大家在饭桌上可能会注意到,同样体重、同样体型的两位男士,有可能一个已经喝醉了,另一个还什么事儿都没有。
所以做惯了毒理学实验的人会知道,那种“给人投点毒让他晕倒或出现点什么状况”的想法,属于影视作品里的科幻成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毒理学家能精准达到他的预期效果。

但是,更最重要的,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澄清的一点是:环境毒理学和传统毒理学也不一样。
传统毒理学研究的是:“人”这种生物在接触到某些化学品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毒性效应。而我们环境毒理学研究的是:除了人之外,这个现实环境中所有其他的生物在接触到某些污染物后会产生的效应,并且,因为这些生物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毒性效应会不会从一种生物迁移到另外一种生物,从一个种群迁移到另外一个种群?——这些才是我们环境毒理学研究的内容。
环境毒理学研究的范畴要比传统毒理学复杂得多。实际上,我们也在现实中观察到:一些化合物在人体内,并不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应,但到了环境中,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例如,DDT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刚刚被发明出来时,曾被很大规模使用。左边这张照片是医护人员在给一个小孩子驱虫,喷的就是DDT。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可能会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感,但在当时,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当然,之所以能这样喷用,也说明DDT对人的毒性确实不是很大。一方面,DDT突破肌肤屏障、进入到生物体内的能力很差,基本上不会因为粘在皮肤上就进到生物体内,另一方面,人类本身也属于对DDT相对不敏感的物种。
对DDT最敏感的是什么?
害虫,那些在农业上需要用杀虫剂杀掉的生物。
在当时,人类眼中的世界只有我们和害虫,所以,安全评估时,只要对害虫有毒性而对人类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就可以了——只是,在大规模使用DDT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后,开始出现一些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
首先,后来我们发现:对DDT比较敏感的不仅仅是“害虫”,环境中其他生物对DDT的毒性也很敏感;
第二,DDT有一个特点:一旦进入到生物体内,就没有退出机制。也就是说,它在生物体内可以一直存留到生物体死亡,然后被释放回环境中。这种现象其实对人类影响比较小,因为人对它的毒性不敏感,人死后一把火烧掉,DDT里的氯元素变成二噁英,也只是再污染一次环境。

但是,环境中,绝大多数生物的死亡方式和人类不同。随着捕食关系,DDT就会从一个生物体进入到下一个生物体,这样一层层累积上去,恰好这条食物链上端的鱼类对DDT非常敏感,在底层影响比较小的毒性,到了上层就明显表现出来。

因为DDT的类激素干扰而造成的猛禽蛋壳变软
除了鱼类,还有一种在食物链中更靠近顶端的生物,那就是很多国家国徽上会出现的的猛禽——它们也是对DDT毒性效应非常敏感的物种。DDT会在猛禽体内产生一种类激素效应,造成蛋壳中钙质没法累积,蛋壳非常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发现猛禽幼雏的孵化率变得非常低,鸟类越来越少了。
这时,有一位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人,也是我们“找茬”专业的鼻祖——蕾切尔·卡森,她注意到,有一种声音消失不见了:春天没有鸟叫了。为此她写了《寂静的春天》,讲述了从DDT开始大规模使用到春天没有鸟鸣的故事。
没有鸟鸣,对于我们人类,可能只是审美意义上的一种缺失;但对那些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就非常深远了。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现在看来可以被视为环境毒理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环境运动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一本标志性书籍——但在它刚刚被发表出来时,公众对它并不认可。为什么?因为它摧毁了一个明星产品,摧毁了一个对人类毒性低、对害虫毒性高,非常好用的农药。它建议“完全停止使用DDT”,但当时,传统农业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想法,同时,很多工业领域特别是有机合成领域的人也开始攻击。
因为提出的是一个“不方便”的现象,所以,“环境毒理学”这个专业从诞生之初就是不受公众欢迎的专业,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听“不方便”的真相。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不仅在鱼和猛禽体内能检测到DDT,即使在从来没有使用过DDT的南极,企鹅体内也检出了DDT;甚至,由于可以通过母乳摄入DDT,婴儿体内也检出了DDT。
恰逢环境运动,加上随后十几年氯氟烃对于臭氧空洞的影响,这些事件,逐渐让环境毒理学专业被公众承认。后来,又出现了几次全球尺度内影响非常深远的事件,人们决定:生产出来的新化学品在使用之前,首先要经过安全评估。这种未雨绸缪式的评估,一方面包括传统毒理学的评估,比如它对人体够不够安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环境毒理学,去评估它对整个生态系统有没有潜在的问题。

我们做这个方向,都希望像蕾切尔·卡森当年一样,找到一个非常好看的靶子,如果能发一篇Science或Nature当然就更好了,毕竟这是科研系统的KPI。
我刚入行时,人们关注的“大IP”是在现代工业合成中才开始出现的纳米材料。当合成的尺度降低到纳米级别、颗粒非常小时,就会出现一些奇异的效应,而这些效应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具体帮助。
我曾经做过纳米二氧化钛的毒理学评估。简单说,纳米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做成的纳米级材料。纳米二氧化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功效:在紫外光的照射下,会产生一个电子空穴,一些有机物可以嵌合在里头,发生一些氧化反应。
比如经典的室内空气污染物甲醛,接触到纳米二氧化钛时,如果有紫外线照射,纳米二氧化钛就会把它拉过来,然后给甲醛强行配对氧分子,这样甲醛在离开时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这其实就是室内空气污染物的一种处理方式。现在纳米级的二氧化钛已经成为市场上很常见的产品,添加在一些涂料里,专门处理室内空气污染物的人,把它粉刷到墙上,再用紫外灯去照射,在这个过程中,墙体内的甲醛就会催化降解。
我对纳米二氧化碳的找茬工作以失败告终了。因为,在研究中发现,因为它颗粒非常小,确实会使人或动物的呼吸系统产生一些炎性反应,但是,当你把它添加在涂料中,固定在墙上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在纳米材料大规模涌现到生产系统中后,全球各个环境毒理学研究小组还评估了纳米二氧化硅、碳管、富勒烯,还有纳米金、纳米银等等纳米材料,并多多少少得出了一些结论。

中间的通道可以作为药物的传递通道,灰色碳管中间那根黄色的细条分子可以是需要被导入的药物
这张图是一根单壁碳纳米管,它插入的这一层中间有像奶油一样的白色芯,上面像蓝莓似的表面是细胞膜的磷脂双分子层。
单壁碳纳米管可以直接插入到细胞膜表面,一方面会引起细胞膜的损伤,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毒性效应,另一方面,它中间的通道可以作为药物的传递通道 ,使那些无法通过细胞屏障的药物(比如抗癌药等等),可以借由这个通道进入细胞。
所以,纳米材料的奇异效应和生物毒性,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我们希望利用它的奇异效应,给我们的工业和生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规避它的毒性效应。而我们环境毒理学家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把它究竟如何产生毒性研究清楚,然后交给环境工程或材料领域的专家,让他们考虑如何解决毒性问题。

这张图是我们做纳米材料毒性研究时观察到的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纳米材料被合成出来时分散在纳米级,到环境中后很快就聚集成团,尺度扩大到了微米级别,一些纳米特性就丧失了,但相应地,纳米的毒性也丧失了。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现在很多领域都在大规模使用纳米材料,因为我们的研究给它带上了安全帽,让它在环境中没有那么明显的毒性效应了。

我的学术生涯在纳米材料这里碰了第一个钉子。之后,我就换思路,开始研究另一类物品。
化妆品中经常会添加一些有香气的物质,给人类使用增加愉悦感。这些有香气的物质,有一些是纯天然的香精,比如提取的植物精油或动物麝香,但它们非常昂贵,尤其是现阶段,我们对于地球资源的开发已经进入一个极限状态。另一方面,很多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其实也能产生香气,可以替代天然香精。

这张图表示的是硝基麝香,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工香料。早先人们把它添加在化妆品中,以更廉价的价格给人们带来愉悦感。在硝基麝香投入使用前,也经过了安全评估,发现它对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毒性。但实际使用中,个别人接触后皮肤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有机合成的研究者就又合成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没有氮原子的多环麝香,作为硝基麝香的替代品。
我主要研究的就是多环麝香,要分析它有没有环境毒性。我首先要想,它到底会对哪些种生物产生毒性效应?
这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其中有大家很熟悉的实验动物,像小白鼠和蚯蚓;也有水生生态学研究里的生产者,比如藻类,以及初级消费者,比如水里游的枝角类的浮游动物大型蚤,还有高级捕食者,比如斑马鱼;另外,我们经常用的微生物是一种发光菌,它在暗环境下可以释放出荧光,非常好看。它们都是环境毒理学里经常用到的实验伙伴。除了畜牧业或兽医,学我们这个专业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动物。
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很擅长养动物。事实上我们的挫败感之一就来自于养动物。

这张图是我一个同学的惨痛经历。她做了6年斑马鱼的博士论文,毕业前,有一天她进到实验室,就看到了上面的场景:前一天晚上锁门时还齐齐整整在鱼缸里的300条斑马鱼,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其实是我们实验室经常发生的问题,也算是科研中的各种不可预料之一吧。
回到多环麝香的话题,我到底应该用什么生物来评估它的毒性?
我的想法是:首先,多环麝香不溶于水,水生生物基本上没机会接触到它,它们应该是安全的;小白鼠可以代表人类去做一些化妆品的敏感性实验,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而多环麝香本身是一种土壤颗粒特别容易吸附的有机物,那我应该考虑一下土壤介质中的生物,所以我选定了土壤中的代表生物——蚯蚓。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蚯蚓染毒。怎么做?
就像在饭桌上给人灌酒。一般人,你刚开始接触他,不知道他的毒性剂量范围是多少,就先给他一小杯酒,如果他喝了,喝完你就可以观察他的毒性效应了:你看他脸白了,是乙醇开始造成毛细血管收缩了;他话变多了,是乙醇产生的欣快感让他打开了话匣子。接着喝,脸红了,那就是乙醇降解成乙醛了,乙醛开始造成毛细血管扩张;然后开始话说不清楚、走路走不齐了,乙醛的共济失调效应开始出现了。这时我就知道,行了。
我们毒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半数有效浓度”,再喝可能就到半致死剂量了。我们做毒理学实验也是类似“灌酒”这样摸索的过程。做预实验时,我们要摸索蚯蚓对于吐纳麝香的毒性剂量到底在哪个范围内,理论上只要你做实验时肯往土里加东西,最终一定能观察到它的毒性效应。
我也确实观察到了。在土壤里加了大量多环麝香后,一开始,蚯蚓的体环会打开,因为蚯蚓爬的动力主要来自体环收缩和舒张,所以,当它接触到一定剂量的毒后,蚯蚓的体环就整个松散,爬动能力变差。如果再继续添加,就会有一些细胞质开始流出来,再继续研究,蚯蚓最后就会死掉。
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人工麝香对环境中典型生态动物的影响——问题是,如果要观察到这种毒性效应,需要在土壤中投入很高的剂量。而人工香料又有一个特点,学术上,称它为有“自限性”的化合物。什么叫“自限性”?就是加多了会让人产生厌恶感,这样就不会使用很多。香料的香气严重依赖于剂量,加的量非常少,会有令人愉悦的香气,加多了就变成了臭气。所以,无论在哪种化妆品中,人工麝香的投加量其实都非常有限。
人工麝香的另外一种污染途径,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跑冒滴漏排放到环境,但相对来说,量也有限。我们做的结果显示,还是需要土壤中有非常大的量才会产生这样的毒性效应。所以我当时就很有挫败感,这样怎么去发文章?怎么挣KPI呢?
没关系,我们做毒理学研究,还有一种套路:当一种东西的毒性不够时,我们就拿联合毒性来凑。因为多环麝香在土壤中产生毒性效应,而土壤中又经常会有重金属污染,所以我们就考虑了镉——这种在土壤污染中同样普遍、毒性也非常大的重金属,看看它们会不会联合起来搞事情。
正常情况下,蚯蚓体内有控制镉毒性的机制,一旦监测到体内有镉,就会合成一些特定蛋白将镉固定起来,这样镉就没法发挥毒性。但我观察研究发现,当多环麝香存在时,蚯蚓体内的这种机制就会被抑制,这时蚯蚓就无法正常应对镉的毒性,镉污染在蚯蚓体内的表现更明显了。这也是我们这项研究里一个相对不错的发现,后来我发表了一篇小论文,挣了一点KPI。
现在,不管是人工香料还是天然香料,消费者也不是非常介意化妆品中添加香料了,不管是天然香料还是人工的——这也可以侧面说明,环境毒理学家已经完成了对这些物质的评估,然后可以放手让它们在工业系统中正常使用。
当然,对于环境毒理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结果,毕竟我们的梦想是像蕾切尔·卡森那样一战成名嘛。
我经常会想起,小时候看的一篇安徒生童话,叫《创造》,大概意思是:有一个年轻人,想当诗人,想创造,结果发现,一切东西已经被写成了诗、被创造过了——
我们环境毒理学家,也常会有这种感觉:当你做研究、做创造性工作时,经常会发现,很多事情别人已经做过了,很少有人会像蕾切尔·卡森那样发现“有一种声音没有出现”。能发现春天的鸟没叫,首先她一定有很深的洞察力,另外一定是在她的专业领域研究非常刻苦、非常精深。我们只有不断努力。
有时也要靠一点运气。
最近这几年,我们环境毒理学家感觉真的来了一波运气,出现了一个“其实一直在房间里,但大家之前都没有看到过”的大象——微塑料污染。
塑料污染,或者说白色污染,是一个很普遍的环境主题了。新中国的第一波环境运动,就是从白色污染的治理开始。之后人们发现,比起陆地上的白色污染,更令人担心的是海洋中的塑料岛——我们陆地上的污染,最终可能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海洋,而在复杂洋流的推动下,它们最终会聚集在海洋中一个特定的位置。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都出现了这种完全由塑料垃圾漂浮堆积形成的塑料岛。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引起环境毒理学家警惕的是:在水力剪切力的作用下,这些塑料会被打成碎片。
微塑料污染最早是被做环境监测的研究者曝出来的。他们发现,大西洋某些位置漂浮着很多粒径很小的塑料颗粒,可能是因为我们会使用一些塑料颗粒,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海洋中的塑料颗粒被打碎了。
环境毒理学家就来劲了,这个我看过,跟纳米材料差不多,纳米材料不就是因为小尺度下产生了奇异特性吗?微塑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最近三四年,微塑料的环境毒性研究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研究热点。
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一些鱼或者水鸟的消化道剖开以后,里面填满了塑料——你们可能都看到过的这种网上图片,触目惊心。
2017年,Nature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分析为什么水鸟放着那么多好吃的不吃,非得吃塑料?为什么打开它的肚子里都是塑料颗粒?
研究发现,因为塑料瓶本身材质是有机质,表面很容易吸附一些有机物,特别是海洋中一些有海鲜味道的小分子。而水鸟在捕食时,主要靠嗅觉定位,所以它很自然地以为这是美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生物那么喜欢吃塑料。

那些有棱角的、一块块比较大的暗黑色物质就是显微镜下拍摄的微塑料颗粒
在微塑料领域,我做的研究是这样:在藻类(水体生产者)的生长体系里加上塑料颗粒,加进去后,那些原本自由分散在水体中的浮游植物会和细菌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共同粘着在这些颗粒表面,使得它最后成了一团。
成团对微塑料颗粒是件好事,因为它变成大块就更容易沉下去,但会让那些藻类生物光合作用的效率明显降低——而水藻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基石,整个水上生态系统获得的能量都是这些水藻通过光合作用搜集到的能量。
另外,我还研究了一个以藻类为食的初级消费者:微型浮游动物水蚤。它是滤食性动物,靠过滤水把食物拦截在它的消化道内。如果藻类被聚集到大颗粒中,它就没法吃到了。所以我们也观察到,微塑料颗粒存在时,大型蚤的摄食效率明显降低,最终会影响到种群的繁殖效率。
可以说,对微塑料环境毒性的研究最近这几年才刚开始,未来预计还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但,做的研究越多,环境毒理学家就越焦虑,因为在大洋中始终存在着一些塑料制品,它们在水力剪切力的作用下,还在持续产出微塑料颗粒。
一方面,从管理的角度,可以从塑料制品本身出发。现在回收再处理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们希望尽量把这些塑料留在生产系统内,不再向环境排放;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环境工程或者其他领域比如材料科学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来处置这些环境中的污染物。
但可以想见,像这样非常小颗粒的物质,处理难度很大。所以环境毒理学家(包括其他做环境工作的人)真的非常烦恼,甚至是焦虑:如果做不出毒性,焦虑发不了文章;做出毒性,又很替地球焦虑。好在可焦虑的事情实在是多,比如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也还在这摆着呢。所以……我们也习惯了这种持续的烦恼状态了。
我经常想,究竟是一个毒性大的物质在环境中的危害大,还是一个毒性小的物质在环境中的危害更大?
我认为,当一种物质毒性很大的时候,它接触到某个个体,很快就会出现毒性效应,这样一方面很容易引起人们警惕,想办法避免接触;另一方面,生态系统本身代偿能力也很强,一些个体的死亡不会对生态结构整体产生明显影响,所以人类也有时间去注意并去解决这些问题。
反过来说,真正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往往是那些微小却非常普遍的存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力量。比如DDT,最终造成危害,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毒性大,反而是因为毒性小,被我们人类忽视了。
作为一名环境毒理学研究人员,我希望我的事业不要太顺风顺水——因为,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像DDT这样帅到惊动老百姓的物质,恐怕我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谢谢大家。

演讲嘉宾王雯《蹂躏完一代代实验动物,我意识到这是一门找茬的科学》 | 摄影:Vphoto
责任编辑:王超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