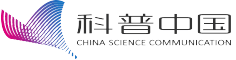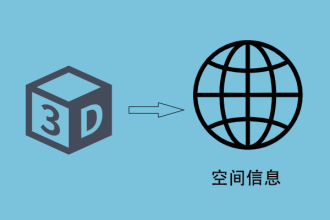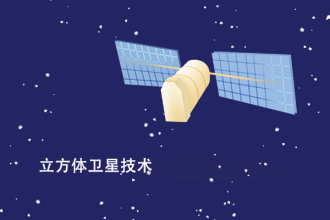数学是发明还是发现的?环球科学 2021-06-16 |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数学有用那是天经地义,但很少有人思考,数学到底是人发明的,还是被人发现的?对于这个让众多学者纠结数千年之久的问题,天体物理学界一位领军人物给出答案:它既是发明的产物,也是发现的结果。
撰文丨马里奥 · 利维奥(Mario Livio)
翻译丨郭凯声
科学家能够推导出描述亚原子现象的公式,工程师可以计算出航天器的飞行轨迹,皆得益于数学的魅力。伽利略第一个站出来力挺“数学乃科学之语言”这一观点,而我们也接受了他的看法,并期望用数学的语法来解释实验结果,乃至预测新的现象。不管怎么说,数学的神通都令人瞠目。
看看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那个著名的方程组吧。麦克斯韦方程组的4个方程,不仅囊括了19世纪60年代时所有已知的电磁学知识,而且还预测了无线电波的存在,此后又过了差不多20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Heinrich Hertz)才通过实验探测到电磁波。能够将如此海量的信息以极其简练、精准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语言,可谓凤毛麟角。无怪乎爱因斯坦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数学本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与实际经验无关,缘何却能与具有物理现实性的种种客体吻合得如此完美,令人叫绝呢?”
1960年,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尤金·魏格纳(Eugene Wigner)以“有用得说不通”来阐述数学的伟大,而作为一位活跃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我在工作中也感同身受。无论我是想要弄清名为Ia型超新星(Ia supernovae)的恒星爆炸产生自哪种前身天体系统,还是推测当太阳最终变成红巨星时地球的命运,我使用的工具以及所建立的模型都属于数学范畴。数学对自然界的诠释是如此不可思议,令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为之神魂颠倒。
这道难题的核心,在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及认知科学家多少世纪以来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数学究竟是如爱因斯坦所坚信的那样,是人们发明出来的一套工具,还是本来就已经存在于抽象世界中,不过被人发现了而已?爱因斯坦的观点源自于所谓形式主义(Formalism)学派,许多伟大的数学家,包括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格奥尔格·康托尔(Georg Cantor),以及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家,都与爱因斯坦看法一致。但其他一些杰出精英,如戈弗雷·哈罗德·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以及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则持相反观点,他们信奉柏拉图主义(Platonism)。
这场有关数学本性的辩论如今仍然火爆,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我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地纠结于数学是被发明还是被发现的这个问题,或许会忽视另一个更为纠结复杂的答案:两者都起着关键作用。我推想,将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应该能解释数学的魅力。发明与发现并非势不两立;虽然消除它们之间的对立并不能完全解释数学的神奇效能,但鉴于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深奥,即使仅仅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一小步,也算是有所进展了。
发明与发现并重
数学“不合理”的神奇功效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依我看其中一种可称为主动方式,另一种可称为被动方式。有时,科学家会针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专门打造一些方法来进行定量研究。例如,牛顿创立微积分学,就是为了了解运动与变化的规律,其方法就是把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分解为一系列逐帧演化的无穷小片断。这类主动的发明,自然非常有效率,因为它们都是针对需要定向打造的。
不过,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所达到的精度更让人啧啧称奇。以量子电动力学(quantum electrodynamics)这个专门为描述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数学理论为例。当科学家运用此理论来计算电子的磁矩时,理论值与实验结果几乎完全吻合,误差仅有十亿分之几。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有时,数学家在开创一个个完整的研究领域时,根本没想过它们会起的作用。然而过了几十年,甚至若干世纪后,物理学家才发现,正是这些数学分支能够圆满诠释他们的观测结果。这类能体现数学“被动效力”的实例不可胜数。
比如,法国数学家伽罗华(Évariste Galois)在19世纪初期建立群论时,只是想要弄清高次代数方程可否用根式求解。广义地说,群是一类由特定范围的若干元素(例如整数)组成的代数结构,它们能够进行特定的代数运算(例如加法),并满足若干具体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存在单位元,拿整数加群来说,单位元就是0,它与任何整数相加,仍然得到这个整数本身)。
但在20世纪的物理学中,这个相当抽象的理论竟然衍生出了最有成效的基本粒子分类方法(基本粒子是物质的最小结构单元)。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尤瓦尔·尼曼(Yuval Ne‘eman)各自证明,一个名为SU(3)的特殊的群反映了所谓强子这类亚原子粒子的某项特性,而正是群与基本粒子之间的这一联系,最终为描述原子核是如何结合的现代理论奠定了基础。
对结的研究,是数学显示被动效力的又一个精彩实例。数学上的结与日常生活中的结颇为相似,只是没有松开的端头。19世纪60年代,开尔文爵士希望用有结的以太管来描述原子。他的模型搞错了方向,跟实际情况基本挂不上钩,但数学家们仍孜孜不倦地对结继续进行了数十年的分析,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深奥的纯数学问题来研究。
令人惊讶的是,后来结理论竟然为我们提供了对弦论(string theory)和圈量子引力(loop quantum gravity)的若干重要见解,它们正是我们眼下为构建一个能够使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和谐统一的时空理论的最好尝试。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在数论领域的发现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代为推动密码学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他本人先前曾断言,“任何人都还没有发现数论可以为打仗这回事派上什么用场”。
此外,1854年,黎曼(Bernhard Riemann)率先描述了非欧几何——这种几何具有某些奇妙特性,例如平行线可能相交。半个多世纪后,爱因斯坦正是借助于非欧几何创立了广义相对论。
一种模式浮现出来: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各种元素——包括图形、线条、集合、群组等——进行抽象概括后,发明出各种数学概念,有时出于某种具体目的,有时则纯粹为了好玩。他们接下来会努力寻找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这一发明与发现的过程是人为的,与柏拉图主义标榜的那种发现不同,因此,我们创立的数学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知觉过程以及我们能构想出的心理场景。例如,我们人类具有所谓“感数”(subitizing)的天赋,可以一眼识别出数量,毫无疑问,这种本能催生了数字的概念。
我们非常擅长于感知各个物体的边缘,并且善于区分直线与曲线,以及形状不同的图形,如圆和椭圆等。或许,正是这些本能促进了算术与几何学的兴起和发展。同理,人类无数次反复经历的各种因果关系,对于逻辑的创立至少也起了部分作用,并产生以下认识:根据某些陈述,我们可以推断出其他一些陈述的正确性。
选择与进化
迈克尔·阿提亚(Michael Atiyah)是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他曾通过一项非常巧妙的假想实验来揭示我们掌握的数学概念是如何受知觉影响的——甚至连数字这类最基本的概念也不例外。德国数学家克罗内克(Leopold Kronecker)有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整数,其余都是人做的工作。”
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世界上有智力的不是人类,而是一种生活在太平洋底与世隔绝的奇异水母,在它们周围,从海水的流动到海水温度与压力,都是连绵不断的。在这样一个找不到什么独特个体,也就是不存在任何离散性元素的环境里,数字的概念有机会破茧而出吗?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数,那还会有数字存在吗?
同水母一样,我们也要采用能够适合于自己所在环境的数学工具——毫无疑问,数学正是因此而显得神通广大。科学家并非随心所欲地选择分析工具,而是根据它们是否能准确预测实验结果来作出选择的。当网球发球机吐球时,你可以用自然数1、2、3依次标示向外蹦出的球。不过,消防员喷水救火时,要想对水流作出有意义的描述,就得用体积或重量之类的概念了。
同样道理,各种亚原子粒子在粒子加速器中碰撞时,物理学家也是用能量及动量之类的指标,而不是用最终到底有多少粒子来评估碰撞。最终粒子数只能给出有关原始粒子碰撞过程的部分信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有其他粒子产生。只有最出色的模型才能历经时间的考验。而那些失意的模型,比如笛卡尔用宇宙物质旋涡来描述行星运动的尝试,就夭折了。反观成功的模型,则会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而逐步改进。
例如,当人们对水星这颗行星的进动获得了极其精确的测量结果后,就必须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来彻底改造牛顿的引力理论,才能对最新测量结果作出圆满解释。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数学概念,寿命都是很长的。比如,早在公元前250年左右,阿基米德就已经证明了球体表面积的公式,而直到今天,这个公式也跟当年一样站得住脚。因此,任何时代的科学家都有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学公式宝库供其搜索,从中找出最适合的方法来使用。
科学家不仅在寻求答案,他们常常也挑选适合于用数学处理的问题。然而,有一大批现象不可能作出精确的数学预测,有时甚至原则上就是不可预测的。例如,在经济学中,许多变量——比方说民众心理素质的详细情况——不适宜作定量分析。
任何理论的预测价值,均取决于各变量之间基础关系是否恒定。我们的分析也无法彻底解读会产生混沌的系统(在这类系统中,只要初始条件有极其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完全不同,因而无法进行长期预测)。数学家们创立了统计学和概率论来弥补上述缺陷,但众所周知,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早已证明,数学本身是存在着固有局限性的。
自然界的对称性
数学能如此成功地诠释自然法则,精心挑选问题与答案仅是原因之一。这样的法则首先必须存在,数学才有用武之地。对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来说,幸运的是我们这个宇宙看起来是被一些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决定宇宙最初结构的引力,同样也左右着今天的星系。为了解释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现象,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发明了对称性的概念。
物理学定律似乎都蕴含着相对于空间和时间的对称性。无论在何时何地,从什么角度来查看这些定律,它们都是不变的。此外,物理学定律对于所有观察者都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这些观察者是处于静止状态,还是在做匀速运动或加速运动。
因此,无论我们在哪里做实验,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乃至在仙女座大星云也好,也无论我们是今天做这个实验,还是10亿年后由另外某个人来做实验,都可以用同样的物理学定律来解释实验结果。如果宇宙不具有这种对称性,那我们想要破解大自然宏伟设计的努力——也就是根据我们的观测结果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可就要无功而返了,因为那样我们就得针对时空中的每个点,不断反复实验。
而在描述亚原子粒子的物理学定律中,则是另一类更复杂的对称性,即规范对称性占据主导地位。由于量子世界的模糊性,某一给定粒子既可以是带负电的电子,也可以是不带电的中微子,还可以是二者的叠加态,除非我们测量了电荷,明确区分出它到底是电子还是中微子。
其实,如果我们把电子换成中微子,或者换成两者的任何一个叠加态,自然界的法则依旧保持同一形式。换成其他基本粒子,情况也仍然如此。没有这种规范对称性,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关宇宙基本运作原理的理论是极其困难的。
同样,没有局域性,情况也会非常棘手(所谓局域性,是指我们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仅受其近邻环境的直接影响,而不受远处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有了局域性,我们就可以首先设法解读基本粒子之间最基础的力,然后利用其他各种知识元素,像拼七巧板一样尝试拼出宇宙的数学模型来。
现今在为统一各种相互作用的尝试中,最有希望成功的一种数学理论,需要依靠另一种对称——超对称性(supersymmetry)。在由超对称性主导的宇宙里,每种已知粒子都有一个尚待发现的伙伴粒子。如果这些伙伴粒子最终被发现[当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投入全能量运行时,它们可能会被发现],那么这将是具有神奇效力的数学的又一项胜利。
在本文开头,我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基本问题:数学是人们发明的还是发现的?是什么因素赋予了数学如此强大的解释能力与预测本领?我相信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数学是发明与发现的精妙融合。一般说来概念是发明的产物,而即便概念之间所有正确的关系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人们依然需要对研究哪些关系进行选择。
现在看来第二个问题似乎更为复杂。毫无疑问,正因我们在使用数学方法时对题材进行了精心挑选,于是数学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有效这种印象。但如果本来就没有什么普遍存在的规律等着我们去发现,那数学就完全无用武之地了。现在你可以这样问:为何会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法则?或者说,为何我们的宇宙被某些对称性以及局域性所支配?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答案,我只能说,在一个不存在上述特性的宇宙中,复杂性和生命或许永远也不会出现,我们当然也就没有机会提出这些问题了。
责任编辑:王超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