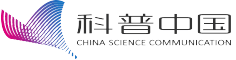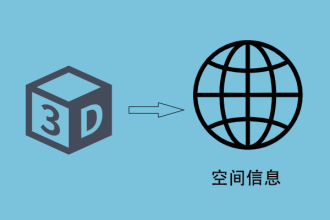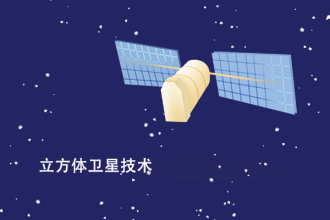这才是传染病的终极解决方案?环球科学 2021-07-18 |
卫生防控和药物治疗曾是20世纪的杰出成就。在研发治疗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上,人类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到了21世纪,科学家在面对一系列新兴传染病时却发现,这并不足以拯救我们。最终能终结传染病的,或许是社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撰文 | 马林·麦肯纳(Maryn McKenna)
翻译 | 赵建元
1972年,澳大利亚杰出的病毒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为《传染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第4版进行了一项调查,十分满意地回顾了20世纪的医学进展。在这一年,美国由于彻底消灭了天花,停止了天花疫苗的常规接种。而在前一年,针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获得了生产许可。在4年前的1968年,一种新的疫苗配方被研发出来,平息了一场大型流感。1960年,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研制出一种小儿麻痹症的口服疫苗;5年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出了第一支小儿麻痹症注射疫苗,用于防止每年夏天儿童因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而出现严重的瘫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天然青霉素开始,已有12种不同种类的抗生素被相继研发出来,它们似乎能永久性地治疗儿童疾病、受伤,以及医疗和分娩过程中出现的致命性感染。
伯内特在这本和戴维·O·怀特(David O。 White)共同撰写的书籍的结尾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关于未来的传染病,最有可能的预测是会非常枯燥。”
伯内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对于人体如何进行免疫反应,他提出了开创性的见解,并与彼得·布赖恩·梅达沃(Peter Brian Medawar)分享了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73岁高龄的他已经经历了多次大型的流行病,包括在澳大利亚读大学时蔓延全球的1918年大流感(1918 Flu Pandemic)。因此,他见证了医学上的很多进步,并在其中一些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书的首页写道:“从人类社会的农业化、城市化到本世纪,传染病一直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现在整个人类的生态模式,至少暂时性地发生了改变。”
仅仅在伯内特给出乐观预测的4年后,在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因不明原因导致的出血性疾病,突然倒地身亡,成为了全球首位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者。在这项预测9年后的1981年,洛杉矶的内科医生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名流行病学家诊断出洛杉矶的5名年轻人患有机遇性肺炎,这是艾滋病在全球流行的第一个信号。
1988年,一种肠道细菌——肠球菌(Enterococcus,是导致医院感染的一种常见病原菌)对最后一道抗生素防线万古霉素产生了耐药性,变成了一种致命的超级耐药菌。1997年,在中国香港的一个市场,H5N1流感病毒毒株从鸡传染到人,导致1/3的感染者死亡,并引起了全球第一波禽流感疫情。
这些流行病仅代表目前每年在人群中暴发的传染病的一小部分。遏制这些传染病,成为现代医学一项迫切的任务。其中一些传染病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全新的,其他则是死灰复燃的老敌人。有时一些传染病会引发小范围疫情,比如2003年在荷兰86名养鸡场工人中暴发的H7N7禽流感。目前,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染性疾病——新冠肺炎的全球性大流行。
没有一幅场景符合伯内特的设想。他认为人类与传染病之间的战争,可以简单地看作一座人类能攀登和征服的大山。但实际上,将这场战争比作一次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的旅程,可能更加准确。有时,我们能成功抵御传染病的浪潮;但是还有一些时刻,例如当前的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击沉我们。
消灭传染病
我们很难完全追溯美国的传染病历史,但可以发现远离传染病曾是早期新英格兰殖民者经历的一部分。从17世纪开始,这些人逃离了充满污水、传染病的英国和欧洲城镇,在那里,活到40岁能称之为幸运。他们发现自己到达了一个受好运眷顾的地方,在新的大陆,男性和顺利生产的妇女的寿命均能够延长一倍。
当然,这只对于这些殖民者成立,而不包括被赶走的美洲土著人。一个世纪前到达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人,以及随后来到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给当地的土著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疾病。研究人员估计有90%的美洲原住民死于这些疾病。但被带到美洲海岸的奴隶并非因此死亡,由于在南方种植园中长期遭受虐待,他们的寿命被极大地缩短了。
历史学家戴维·K·罗斯纳(David K。 Rosner)说:“在19世纪之前,新英格兰人具有一种非常奇怪且不寻常的传染病经历。”罗斯纳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历史与伦理中心的联合主任,他表示:“当传染病袭来时,他们确实感染了天花、黄热病,但大多数感染都是非常局部的,且持续时间较短。”
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初期,患上疾病会被认为逾越了道德。而疾病降临到患者身上,是为了引导错误的人回归正途。1832年,一场全球性的霍乱大流行冲击了美国东海岸,往来于贸易航线的船只将病毒带入港口城市。十几个州的州长宣布进行一天强制性的祈祷和禁食。居住在纽约市区的富人逃离城市,前往了与世隔绝的乡村,并把自己遭受的不幸归咎于留在城市的穷人。纽约历史学会(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保留着一封由创立者写的信,反映了当时一些富人的麻木不仁:“那些恶心的穷人……是城市里主要的渣滓,越快把他们赶走,疾病就能越快停止。”
霍乱是一场全球性灾难,但它也是我们了解现代疾病的一个窗口。传统的教条认为它的起源是瘴气、来自腐烂垃圾的污浊空气和死水。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追溯到伦敦霍乱暴发的源头是一口井,并通过移走泵柄,阻止了疫情的传播。
20年后,也就是在1874年,一次关于霍乱的国际会议宣称“空气是霍乱传播的主要媒介”。(如今的研究已经证实,霍乱主要通过食物、水源、接触患者和媒介昆虫传播。)又过了10年,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在印度多个霍乱感染者的粪便中发现了同一种细菌,在利用培养基繁殖了该细菌后,他最终证明这种微生物是导致霍乱出现的原因。当时,科赫并不知道意大利细菌学家菲利波·帕奇尼(Filippo Pacini)在斯诺移走泵柄的那一年,也做过同样的观察。
关于霍乱起源的解释成为了细菌学的一个基础理论。疾病能传播、传播媒介可以被识别甚至可能被阻断的概念,改变了医学和公共卫生学。这一观念也激起了市民的决心,他们开展了一场城市清洁运动,因为城市中肮脏的道路会促进致病微生物的繁殖。各乡镇和州设立了市政卫生部门和环卫局,负责修建排污系统和长距离供水系统,监管食品安全和下令住房改革。
这些改进使一些工业化国家实现了流行病学转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这个概念由后来的阿卜杜勒·奥姆兰(Abdel Omran)于1971年提出,用来描述社会中致命的传染性疾病消退,慢性疾病上升为主要疾病的时期。科学家们也开始向20世纪医学的高峰攀登,势头一度似乎不可阻挡:鉴别病毒、改良疫苗、研发抗生素、开创免疫疗法和解析人类基因组。美国的人均寿命也由1900年的47岁,上升到世纪末的76岁。医疗记录显示,最后一例天花病例出现在1978年,而天花也成为了唯一一种被人类根除的疾病。1985年,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宣布美国消灭了小儿麻痹症。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生物医药的崛起,人类的未来似乎是安全的。
新的传染病崛起
但是,当然不是这样。1988年10月,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和卢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在刊登于《科学美国人》的文章中写道:“1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在发达国家,传染病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公共卫生面临的剩余挑战将来自于各种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心脏病和各种退行性疾病等。但是,这种信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艾滋病的出现而破灭了。”
加洛和蒙塔尼耶在不同国家的研究团队中分别独立发现了HIV。当他们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全球的艾滋病病例已经超过了77000例(现今大约有7500万例)。正如他们在文中所指出的,对这种新疾病的认识打破了人们认为已经征服了传染病的盲目自信。在加洛和蒙塔尼尔撰写文章的4年后,美国医学研究所召集了19位杰出科学家,对这种“新兴传染病”进行了清晰和详尽的书面评估。他们表示,科学家和政治家已然变得十分自满,对抗生素和疫苗能提供的保护充满信心,却忽视了人口增长、气候变暖、快速的国际移动以及破坏野生环境以建设居住地和大型农场带来的传染病威胁。
这个科学家组织警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遥远的,每一个人都密不可分。”他们建议快速改进疾病检测和报告、数据共享、实验室的生产能力,以及抗生素和疫苗的研发。他们说,如果不在这些方向上加大投入,人类在面对新的传染病时将会一直落后。而在采取的任何预防或治疗措施能阻止疾病传播之前,我们可能已经面临着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的警告很有先见之明。在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20世纪60年代就正式接种麻疹疫苗的美国,开始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麻疹疫情复苏。当流行病学模型预测3年内的麻疹感染病例会少于9000例时,而实际上,患者的数量上升到了5万多人。
在美国医学研究所发表这篇报告的第二年,美国西南部有5名健康的年轻人死于一种来自白足鼠(Peromyscus leucopus)的汉坦病毒。1996年,芝加哥的研究人员发现,耐抗生素的葡萄球菌已从此前只在医院出现扩散到了日常生活中,这给那些处于未知感染风险中的儿童,带去了致命性的疾病。在整个医疗保健领域,无论来自城市还是自然界的病原体,似乎都在让数十年的医学发展成果开始土崩瓦解。
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凯瑟琳·赫希菲尔德(Katherine Hirschfeld)说:“我们忘记了猖獗的传染病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我们通过发展科学建立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随后变得过度自信,决定不再对传染病研究投入人力和资金。”
但是,不同于过去流行的疾病——霍乱流行是由于富人逃离城市,结核病暴发和瘟疫归因于移民,而艾滋病让同性恋者遭受污蔑——如今的流行性疾病传播不再能轻易找到“替罪羊”。没有一个地方或人可以做到完全与社会隔离,全球化贸易、国际旅行和人口流动会使所有人受到疾病的伤害。赫希菲尔德说:“我们再也无法把世界划分为成功应对传染病和仍处于挣扎中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中,富人和穷人的居住地相互交错。任何人都无法避开患病风险。”
放松警惕
在20世纪的自信浪潮中,整个世界对传染病的关注开始滑落,这也促成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在新冠病毒开始广泛传播的5年前,至少有大量警告提示可能会出现一种突发的全球性传染病,这些警告出现在学术论文、联邦政府报告、智囊团的战争游戏以及移交给白宫新执政党的档案中。
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我们已知的防御漏洞传播,它是一种源自野生动物的疾病,能感染近距离接触和捕捉动物的人类,随后利用快速的人群流通传播。由于缺乏充足的监管,人们对其放松警惕,而政治民族主义和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再次放大了疫情。
对于这次疫情,我们毫无准备,没有任何应对的疫苗或抗病毒药物。在应对过去流行的冠状病毒疫情,比如2003年的非典(SARS)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时,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疫苗,但是随着疫情消退,他们的科研兴趣和研究经费也随之丧失。如果这些研究继续进行,目前紧张的疫情情况将会有所缓解。预防和药物治疗曾是20世纪的杰出成就,但是科学家和医生意识到在面对新发疾病时,试图重复这些成功将不足以拯救我们。他们认为,同样紧迫的是关注和改善促使新发疾病产生的环境。
“贫困对疾病传播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干预措施,”彼得·J·霍特兹(Peter J。 Hotez)说。他是一名医生和疫苗开发者,也是贝勒大学热带医学学院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政治崩溃、气候变化、城市化和森林砍伐,这些都是阻碍我们前进的因素。我们可以开发出所有想要的疫苗和药物,但除非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否则我们将会永远落后于这些传染性疾病,”霍特兹说。
霍特兹的说法获得了充足的证据支持。在当前的疫情中,那些依赖城市交通、住在公共住房或疗养院、长期受到种族主义影响的人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而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缺乏药物或疫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其首席医疗官和传染病医生布拉德·斯佩尔伯格(Brad Spellberg)说:“我们的医院全是新冠肺炎患者。我们服务的社区居民之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他们无家可归,生活贫困到四口之家必须住在一个房间里。”
霍特兹和斯佩尔伯格所描述的内容通常被称作“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词语,没有“注射疫苗”和“药物”那样直截了当,但它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可以衡量的概念:社会和经济因素而不仅仅是医学或个人的先天免疫力,会强烈影响感染疾病的风险。负面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住房不安全、医疗保健不足、就业不稳定甚至是缺乏政治代言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肝炎、性病、寄生虫感染和介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迅速上升。正如2018年《科学美国人》所报道的,在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中会首先出现感染,随后疫情会蔓延到富人和有社会保障的地区。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中最富裕和最贫穷人群的收入差距越大,该国越有可能出现更短的预期寿命、更高的慢性病患病率、少女(15~19岁的女性)生产率和婴儿死亡率。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在政府采取封锁和强制措施之前,为什么新冠疫情对纽约市(美国经济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
能阻止或减少疾病的可能是更繁荣的经济和更平等的资源分配。南亚的村民将不需要捕捉和出售蝙蝠,来补充经济收入;而美国的低薪工人拥有病假,而无需带病工作。即使不是因为流行病,这也是一项公平的社会转变。
更好的预防措施
一个更具有保护性的社会如果没有如下列举的特征:更好的住房及医疗条件、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它看起来就会像是一张模糊的愿望清单。不过,全球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预防措施,可能会降低未来感染的风险。一些提议希望美国像里斯本一样设置自行车专用道以鼓励人们骑车,模仿巴黎将停车位转变为咖啡厅位,并创建宽带用于远程办公或将医疗服务转变为远程医疗。这些改变听起来像是技术乐观主义,但实际上可以帮助构建一个人们不必拥挤在城市中心,工作的地理环境与收入分开的更安全的城市。
当然,我们还必须重新增加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上的经费投入。美国医学研究所指责美国几乎在30年前就减少了这方面的投资。“我们需要用保险的心态来考虑这个问题,”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主席、内科医生哈维·法恩伯格(Harvey Fineberg)说。当法恩伯格2003年担任该研究所主席时,曾针对这项警告,策划了后续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说:“如果你的房子没有被烧毁,你会在年末用头撞墙,后悔为什么买了火灾保险吗? 我们主动购买这些保险,是为了防止不良的后果。这是我们在应对大流行病时需要采取的心态。”
毫无疑问,现在的医疗水平比伯内特写作时的上世纪70年代要强大得多。在单克隆抗体药物、基因治疗、针对癌症而不是微生物的疫苗出现之前,《自然传染病史》早就出版了。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典范可能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的研发,该疗法于2017年首次亮相,它可以通过重新激活人体自身特定的免疫系统细胞,来对抗癌症。
但是,CAR-T疗法也标志着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已经跌入了谷底。CAR-T疗法由于价格高昂,只帮助了极少数病人,在进入任何医疗保险之前,它的价格一直高达50万美元左右。抗生素疗法曾让数百万人免于死于感染,现在其研究却陷入危机之中。上世纪70年代,大多数生产抗生素的大型制药公司,例如礼来(Eli Lilly)、阿斯利康(AstraZeneca)、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和诺华(Novartis)等,都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而离开了这个药物领研。虽然抗生素在医学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但这种情况依旧在发生,而现在愈发明确的是,一些新冠肺炎患者需要抗生素来治疗感染初期出现的严重肺炎。
为了预防传染病,更有效的医疗结构包括疾病监测、为新药和疫苗研发提供经费、快速检测和实行全面报告。这些措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起点,一个能让我们远离已知疾病的更安全的社会,并更有可能发现未知的威胁,以全新的医疗条件予以回应。
历史学家罗斯纳回顾了美国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爆发的生产力,设想着新冠疫情之后会有出现哪些重大的改变。他说:“在19世纪,我们在整个社会建立了供水系统,让城市中的每条街道保持清洁。我们或因为过于限制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因而感觉似乎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过去的危机中,我们时常会看到社会中更美好的事物在危机中出现。比如,在经济大萧条后,出现了让美国重新恢复的罗斯福新政。这一切再次发生,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本文作者:马林·麦肯纳是埃默里大学人类健康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公共卫生、全球卫生和食品政策记者。
本文译者:赵建元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抗病毒药物。
责任编辑:王超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