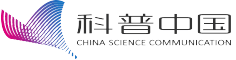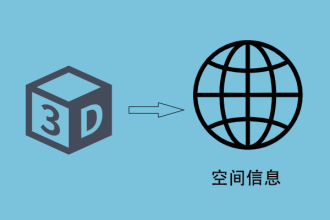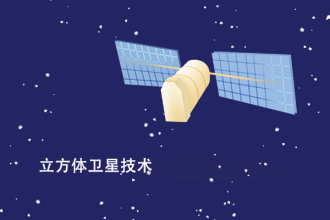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我们,都得了“反替身综合征”授权果壳网 2016-11-25 |
(译 / 玛雅蓝)我们从一个女人的案例说起,她有着不堪忍受的悲惨经历。1899年,巴黎的一位新娘M夫人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孩子被拐走了,被换成了另一个婴儿,后者很快夭折。随后,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健康地长到了成年,而另一个再次被拐走,换成了一个死婴。后来,她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被拐走,另一个被投毒致死。
M夫人努力寻找被拐走的婴儿,但她显然不是这种噩梦般的创伤唯一的受害者,因为她时常听到一群群被拐走的孩子在巴黎的各个地下室里嚎啕大哭。
这还没完。就好像她受的苦还不够多似的,M夫人唯一幸存的孩子也被拐走,被换成了一个外貌完全相同的替身。很快,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M夫人的丈夫身上。这个可怜的女人日复一日地寻找她被拐走的所爱,同时试图把其他被拐走的孩子从藏匿处解救出来。她还开始准备书面材料,要和那个取代了丈夫的人离婚。

在世纪之交,法国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卡普格拉(上图)猜想,幻觉能够反映某些大脑疾病。但在弗洛伊德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之下,他也跟上了心理动力学的潮流。(插图作者:Jackie Ferrentino)
1918年,M夫人请求警方协助她解救一群被锁在她家地下室里的孩子。不久后,她和一位精神病学家谈话。她告诉他,她是路易十八的直系后裔、东印度群岛的女王和萨兰德拉(译者注:意大利的一个市镇)公爵夫人;她有一大笔财富,价值在2亿到1250亿法郎之间,但她在幼年时就被人取代,这是一个阴谋,以夺取她的钱财;她一直受到监视,而且她遇到的几乎所有人都被替身所取代,有时甚至是替身的替身。
这位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卡普格拉(Joseph Capgras),耐心地听着她的讲述。他心想,这是妄想性精神病(delusional psychosis)——思维混乱,自大,偏执。非常符合诊断标准。然而,心爱之人被完全相同的替身所取代,这种幻觉此前从未被描述过。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后来,在关于M夫人的案例报告中,卡普格拉和他的助理让·勒布尔-拉绍(Jean Reboul-Lachaux)写道:“她的陌生感不断上升,并和熟悉性展开了竞争,而熟悉性存在于所有的再认过程中。但是,陌生感并没有完全占据她的意识,也没有扭曲她的知觉或记忆影像。”对卡普格拉来说,这个案例非比寻常。在M夫人身上,再认(recognition)和熟悉性(familiarity)唤起了不同的情感,而她的问题就在于无法协调这两种情感。替身综合征不是来自于感官的错觉,“而更像是情感判断的结论”。
相信亲近的人被完全相同的替身所取代,精神病学家将这种错觉称为“替身综合征”,又叫“卡普格拉妄想综合征”(Capgras delusion),它不仅仅是只存在于档案中的特例。大脑中存在着相互独立的模块,分别负责在认知层面上进行辨认,和在情感层面上感受熟悉性。对替身综合征的理解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两个模块的大量信息,它表明尽管认知和情感可以在神经生物学上分离开来,但只有当它们密切协作的时候,人的行为才会更加合理。
作为一名现代的神经科学家,我认为关于替身综合征的历史记录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反映了我们对于大脑和行为的看法所发生的变化。这种疾病最初是那些认为心智与大脑之间联系甚少的科学家的“专利”,对于他们来说,替身综合征就和所有的妄想症,以及精神病学档案里所有其他疾病一样,是一个关于心智与心理的形而上的问题。
但是,自从21世纪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每种想法、情感和行为都是实体的大脑的直接终端产物。替身综合征就产生于大脑的物质基础,这个机制能大大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产生再认的思维和引发熟悉性的感觉之间存在多少差异。
正如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社会脑中存在着功能上的断层,它们和网络世界的发展共同塑造了当今的“脸书一代”。这一代人已经使妄想综合征成为了窥见当代文化和思想的一扇窗口,在这里,一切都面目模糊,但又都似曾相识。
***
M夫人的妄想似乎能够完美地被解释为她对于自身创伤经历的反应。在她产生关于投毒和拐骗的妄想的那段时间,她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在婴儿期夭折。当真实悲惨至此时,现实里的许多事可能远比“你的孩子还在某处活着”这样的保护性妄想要糟糕得多。但当时的精神病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创伤导致了大脑的生物学性损伤,从而引发妄想。
相反,对替身综合征成因的理论研究拐向了精神动力学的方向。弗洛伊德早在1911年就提出,妄想来自被强烈压抑的欲望。这种通用的解释很快就被套到了替身综合征的案例身上。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主流精神病学界已经达成一致,为替身综合征作出了精神动力学上的标准解释。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性压抑,以及我们对于最亲密的人所共有的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内心不够强大的人将无法处理这种矛盾,从而发展出替身综合征——所爱之人必须被分裂成一个坏的版本(替身)和一个好的版本(被诱拐的那个人)。大功告成!(不过,这无法解释为什么M夫人对巴黎的一大半人口都怀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情感,以及为什么一些替身还会拥有自己的替身。)
有了这样的弗洛伊德式解释,关于替身综合征的讨论常常围绕疾病的分类展开。有人认为替身综合征是一种独立的疾病,有其独特的精神动力学成因;也有人认为它不过是精神动力学中“幻想错认综合征”(delusional misidentification syndrome)的一个分支。这类疾病还包括:弗雷格利综合征(Fregoli delusions),患者会将许多不同的人视为同一人的伪装;虚无妄想综合征(Cotard’s syndrome),患者感到自己的血液或一些器官神秘消失,甚至根本不存在;还有复制记忆错构症(reduplicative paramnesia),即认为一个熟悉的地方被复制和替换了。与此同时,那些专注于分类学的精神病学家把所有这些疾病和其他常见的妄想症划为一类,统统丢进精神疾病的分类之下。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妄想综合征一直静静地待在精神病学的王国中。到了六七十年代,人们开始确定这种妄想也可能出现在患有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症等精神障碍的患者身上。但这并没有对它在分类学上的位置造成多少影响。毕竟,如果你的记忆已经严重减退,无法认出亲近的人,那么如果他们自称是你的亲属,这就显得很可疑了,就像是替身的行为。(我父亲在严重痴呆的末期,曾经情绪激动地对我的母亲喊道:“我老婆在哪?我真正的老婆!你不是我老婆,你是个什么,什么共产党人!”)尽管其他种种妄想都被赋予了精神动力学上的意义,由痴呆所产生的替身综合征症状却曾经被视为普通的妄想症和虚构症,是认知功能受损的副产品。
尽管如此,在20世纪最重要的医学革命之一的冲击下,替身综合征的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在五十年代,人们发现可以用药物阻断某种特定的神经递质受体,以治疗精神分裂症,其疗效远胜于多年的心理治疗。这催生了一种新的认识:所有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基础,在生物学上,那些反常行为和神经精神障碍就像糖尿病一样“真实”。
讽刺的是,在投奔精神动力学之前,卡普格拉本人在早期的记录中曾简单提出猜想:幻觉可能反映了某些脑部疾病。随后,1930年的一篇论文尝试提出类似的猜想,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量研究之后,下面的两个事实才得到了承认。
首先,如果检查替身综合征患者的大脑,常常能找到脑部疾病的明确证据。人们很晚才认识到这点,主要因为早期的脑电图(EEG)技术只能观察到一小部分患者身上的异常。但随着脑功能成像等更灵敏的技术手段不断出现,我们可以确定有相当一部分替身综合征患者患有器质性脑部疾病,通常和额叶皮质的损伤或萎缩有关。
第二个事实相当于第一个事实的反推:如果大脑受损,尤其是额叶皮质的某些区域受损,那么患者有时会发展出替身综合征。
2013年的一个案例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位女性的右侧额叶皮质发生了脑出血,经过多年的康复治疗后,她的大脑功能基本恢复,只是存在一些空间定向方面的后遗症。而且,尽管她能够轻松认出大部分亲朋好友,包括女儿和外孙们,她仍然坚持认为丈夫已经被一个替身所取代。是的,是的,她承认,他看起来很像我的丈夫,在我的康复过程中也给了我不少帮助,但他肯定不是,我丈夫在别的地方。她能毫无困难地认出丈夫的照片,却认为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他。她还相信自己的家已被一个完全相同的复制品取代了。
替身综合征已经被划入严重神经系统损伤的范畴。弥散的脑部损伤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尽管可以识别心爱之人的特征,却坚持认为眼前这位大活人是个替身。这种现象最终告诉我们,心物二元论是关于大脑最严重的误解之一。
至少从笛卡尔的时代开始,将“心灵”和“大脑”对立起来的二元论观点就已经存在,或者“认知”与“情感”,这是更受近代神经科学家青睐的衍生说法。在标准的二元论中,认知与情感在功能上和神经生物学上都是可分离的,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永恒的、史诗般的斗争,以争着掌控你的行为。这种二元论甚至催生了一种观点:二者之一应当占据主导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伦理学和美学的混合产物。
现在我们知道,将认知和情感完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玛西奥(Antonio Damasio)在1994年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一书中清楚论证了这一点。认知和情感始终在功能上和神经生物学上相互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们最好能密切协作,因为哪怕我们眼中的普普通通的功能,都需要两者之间的高度协调。
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就体现了这种协调,尤其是在情感唤起的环境中。前额叶皮质中有两个关键区域。首先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大脑中最“聪明”、认知能力最强的部分,同时也是在演化上出现得最晚、发育成熟最慢的区域。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选择性损伤会让人做出糟糕的决策,患者往往性格冲动,无法延迟满足,且无法根据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决策情境下,这样的人能说出最优策略——“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要等待下一轮奖赏,因为它的价值要高得多”,但他们却无法控制自己,仍然选择较差的即时回报。
此外,还存在一个“感情用事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它是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之间的桥梁。如果这个区域受到单独损伤,患者也会做出糟糕的决策,但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这些患者极其优柔寡断,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某种“本能的”直觉。而且,他们的决策更冷酷无情、实用主义。比如,当遇到一个人的时候,患者可能会说:“你好,我看你真胖啊。”而当他们因此而受到责骂时,他们会困惑地回答说:“但我说的是真的。”
当需要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所认为恰当的行为其实反映了情感和认知知觉的平衡,尤其是在社会环境中。而替身综合征告诉我们,要认出最熟悉的人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平衡。
我们怎样认出自己心爱的人?嗯,我们知道他眼睛的颜色;他的头发有独特的质感;他有特别的姿态;他下巴上有童年时留下的伤疤……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负责这项任务的是灵长类动物大脑中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区域——梭状回(fusiform gyrus),它负责识别面孔,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面孔。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会怎样识别那个重要的人?嗯,我们会重新想象第一次将她拥入怀中的感觉;靠近她的时候,她的气味唤起了无数的回忆;我们捕捉到她脸上掠过嘲讽的微笑,从而知道她也觉得晚宴主人很无聊……都是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在神经科学上,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面孔识别外延系统”(extended face processing system),这是一个分散的网络,包含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中的多个区域。
身份识别就处在事实认知和熟悉感之间的交叉领域。在这个框架之下,当面孔识别外延系统受到了选择性损伤,导致熟悉感受损,就产生了替身综合征。患者的面孔识别能力是完好的,他们知道眼前的人看起来和心爱之人一模一样,但就是觉得陌生。
在2013年的那项研究中,患者在脑出血后产生了关于丈夫的替身综合征。她被要求观看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面孔,并接受脑部成像检查。在控制组的被试身上,这两种面孔都激活了梭状回面孔区,而熟悉的面孔还激活了大脑中和注意力有关的区域,以及情感和记忆的交叉地带。那个患有替身综合征的女人呢?她的梭状回活动正常,然而其他的区域没有被激活。她的面孔识别功能仍然健全,但那张面孔的情感意义却消失了。
但这只是导致这种幻觉的一部分原因。假设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你亲近的人说了些反常的话,或者做出了反常的事,让你觉得很陌生。我们会想,那可不像他!但我们不会因此认为他被一个完全相同的替身取代了,而是会寻找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他最近没睡好。引发妄想综合征的神经损伤不仅破坏了熟悉感,也破坏了思考和评估的能力,而那些能力能让人放弃荒谬的替身妄想。然而,替身综合征患者常常观察得极其仔细,以试图解释他们眼中荒诞的世界。“啊哈,那谁的门牙之间是有一道缝,但没有这个冒牌货的牙缝那么宽。哥们,干得漂亮,但还不够好。”
替身综合征患者的面孔识别能力健全,但熟悉性受损,这在神经病学上恰好有一个反例。1990年,英国的海顿·埃利斯(Hadyn Ellis)和安德鲁·杨(Andrew Young)最先发现了面孔失认症(即脸盲症,prosopagnosia),这是一种认知缺陷,常伴随着梭状回损伤。患者再也无法识别面孔,无论是亲近的人、明星还是历史名人。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患者可能会退而求其次,运用其他正常功能,采用接近机械算法的方式来识别他人。“嗯,这个人到医院来看我了,他的脸是这个形状,还有这个特别的胎记……对,他是我老公。”
面孔失认症为何会成为替身综合征的镜像?对于前者来说,尽管他们的认知功能受到了损失,熟悉性还在哪儿。如果对面孔失认症患者展示一系列的面孔,他们会说:不,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我也不认识。如果图片上出现了他们亲近的人,你也会听到同样的否认——“哎,不认得!”但是,他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却对熟悉性作出了响应,心率和皮肤电传导率都发生了改变。再认被激活了。尽管你坚信自己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张脸,你的大脑却清楚地知道他是谁——他是那个给我安全感的人,自从我们共同生活开始,他的微笑、他的身影和他的气味曾伴我迎来每一个清晨。

你是谁?和替身综合征一样,脸盲症也体现了再认和熟悉性之间的裂痕。一些有趣的绘画就体现了那种努力识别一个好友的感觉,例如《罗伊,我》。这是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的肖像,作者查克·克罗斯( Chuck Close)本人也经受着脸盲症的困扰。(图片来源:Chesnot, Getty Images)
替身综合征和面孔失认症,这两种互补的精神错乱揭示了破坏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微妙平衡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在我们的大脑中,那些相互独立的模块各司其职,但如果切断它们的功能之间的联系,我们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正是认知和情感之间的断层,或者说再认与熟悉性之间的断层,使得替身综合征成为我们今天精神状态的一种隐喻。
在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里,社交行为都由面对面的互动构成,社交的对象是你大半辈子一起狩猎和采集的人。但是,在现代技术的作用下,构成再认和熟悉性的“元件”正在日渐分离。这里的“现代技术”指的是在最近几千年中出现的技术——用墨水在纸上写下一些记号,将它送到远方,让对方破译它,你就能和别人交流。然而,要认识一个人,靠的是他们的微表情、散发的外激素和整体形象,而不是信上的单词使用频率或签名笔迹这些隐晦的信息。我们作为灵长类动物所拥有的熟悉感,就这样遭受了技术带来的第一次冲击。自此,技术带来的挑战呈指数增长。这条短信是我亲近的人发来的吗?它感觉熟悉吗?看情况吧。他们喜欢用什么表情符号?
因此,现代生活不仅日渐加深了再认和熟悉性之间的鸿沟,在此过程中它还损害了后者。我们出色的多线程技巧则让情况变得更糟,尤其是多线程社交。美国佩尤研究中心近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89%的手机机主在最近一次社交集会上使用了手机。我们把社会联系缩减成可怜的信息流,以便同时维护尽可能多的联系人。在这样的交流中,熟悉性变得支离破碎,只剩下一点儿可怜的残留。
这可能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面对替身的时候变得越发脆弱。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现实的仿品,还有仿品的仿品。在网络上,我们接触到的人自称认识我们,想要帮我们修复网络安全漏洞,或者邀请我们打开他们发来的链接。而其中有些人可能与他们自称的身份并不相符。
按理说,这本该让我们所有人患上替身综合征,相信自己碰到的每个人都是替身。毕竟,当你把所有的钱打给了一个自称国税局工作人员的家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怎能不受到冲击?
然而,事实却和逻辑推论很不一样。在技术的冲击下,熟悉性日渐消亡,这反而让我们把普通熟人误认为知心朋友,仅仅是因为两人在阅后即焚(Snapchat)上有过亲密的互动,或者关注的脸书主页完全一样。我们与别人变得亲密,随后却发现这种熟悉性是虚假的。毕竟在现代,哪怕我们没有闻过对方发间的气味,也能在网络上坠入爱河。
在整个历史上,替身综合征都如同一面镜子,展示了一个分裂的头脑,其中理性的认知与感性的亲密发生了分离。现在,它仍然是那面镜子。今天,我们将周围世界中虚假的、人造的事物视为真实的、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将爱人和朋友误认为替身,而是将替身当成了他们。(编辑:游识猷)
责任编辑:lijia
上一篇:为什么这个地方令人幸福感飙升?
下一篇:带你走近夜晚工作的科学家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