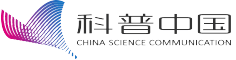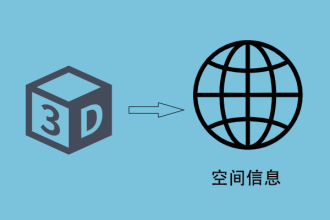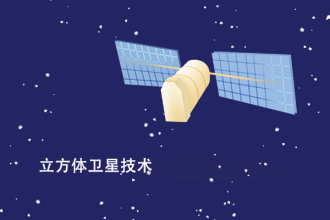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人类基因组正在衰败把科学带回家 2019-12-02 |
过去的致命疾病在现代社会不再致死,人类因此摆脱了自然选择,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早在70年前,科学家就注意到人类基因组正在不断累积基因突变,而其中大部分突变是有害的。以人类的低生育率要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许多科学家们为人类的未来感到十分忧虑。
参考资料 Nature 等
编译 七君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现在患有近视眼、过敏、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的人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病,很可能是逃离了自然选择后,人类患上的现代病。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疾病是人类基因组正在缓慢衰败、累积有害突变的征兆。
随着大量证据的出现,这个现象也被命名为突变载量递增(increasing mutational load)。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 DNA 发生的变化说起。
你的 DNA 是你的合成蓝图,它们一半是来自你妈的拷贝,另一半是来自你爸的拷贝。但是拷贝的过程中,DNA 会出错,这就是突变。我们出生时,平均每个人拥有100个爸妈没有的新突变。
虽然不是所有的突变都是有害的,但要是在史前,携带多种有害突变的孩子恐怕没法活到生子,甚至都无法养活自己,他们的基因无法进入人类基因池,而被自然选择淘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祖先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经历了残酷的自然选择。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DNA 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但是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比祖先们的要友好得多,许多致死疾病也不再致命,自然选择的作用开始减弱。
比如,20世纪初的时候,携带I型糖尿病(一种高度可遗传的糖尿病)的风险基因的人一般会早死,服从自然选择。但是现在,这些人可以终身使用胰岛素,过上正常的生活,生儿育女,把他们的有害突变遗传下去。
和I型糖尿病类似,不少突变导致的疾病在现代社会里能得到更好的治疗,过去的致命疾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靠药物可以控制,因此相关基因突变也不会从基因池中被剔除。
实际上,科学家们对小鼠、蠕虫和其他许多动物的实验发现,在没有自然选择的情况下,实验室动物的突变发生率会不断增长,整个种群会变弱,适合度(生物个体或群体适应环境的程度)降低。
换言之,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基因池成了有害突变的避难所。
自然选择下线
最开始发现人类基因组不断累积突变的现象的是美国遗传学家,因为发现X射线诱导突变而获得诺奖的 Hermann Joseph Muller。Muller 在大约70年前发现了这个惊人的现象。
Muller 当时的研究发现,有害突变会不断产生,平均每个新生儿带着50-100个新的突变出生。这还不算,我们已经从父母和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大坨有害突变了。而纵观人的一生,每次细胞分裂,都会收获3个突变。
Muller 担心,不再受到自然选择的诸多限制,甚至开始操纵自然的人类要为此买单,承受由于缺乏自然选择带来的“自净”功能而导致的恶果。
即使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Muller 的担心也并不多余。50年代,美国在大量测试核武器,辐射尘埃在大气中四处散播。发现X射线诱导突变的 Muller 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他担心核武器试验将要将人类逼上灭绝的道路。
雪上加霜的是,Muller 还发现,人类基因组里有很多基因连锁群(linkage group),相当于捆绑销售(遗传),无法拆开的一群基因,它们不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
有害基因会影响这些基因连锁群,产生连锁反应。这就是著名的缪勒氏齿轮(Muller's ratchet)——基因连锁群只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不会反弹,就像无法反转的齿轮一样。
意识到了这点后,在1950年的 Our load of mutation 一文中,Muller 指出,如果突变率太高,人类基因组会不可避免的恶化,最终导致人类灭亡。
“很难解释人类是如何幸存的”
那么,人类的突变率究竟有多大呢?
在 Muller 眼中,突变率高于0.5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每代每个人的突变应当不超过0.5个,这样才能保证人类不会灭绝。
2018年,在一次美国卫生研究院(NIH)的演讲中,研究了突变载量18年的康奈尔大学的遗传学教授 John C. Sanford 指出,“学遗传学的人都知道,人类基因组累积了越来越多的有害突变,突变载量太大。现在科学家们的共识是,人类突变的速率是,每代人的每个人平均贡献了100个突变,”远远超过 Muller 给出的数字。
来看一些具体的研究。
1997年,生物学的另一位大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遗传学家 James F. Crow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论文发现,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有害突变一直在不断累积。Crow 估计,有害突变导致的繁殖能力下降率大概是每代人下降1-2%。
无独有偶,1996年,一些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的研究者在对人类线粒体基因组(线粒体里也有DNA,和细胞核里的DNA不同)测序后,也发现人类线粒体基因组累积的突变太多。在这篇被引用了260多次论文中,他们发问:“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带有这么高突变载量的系统如何演化下去。”
更糟糕的是,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所有的非中性突变都是有害突变。
作为证据,1999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生物学家 Adam Eyre-Walker 和爱丁堡大学的生物学家 Peter D. Keightley 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的基因突变率非常高,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有益突变,大部分是有害的。这项研究目前被引用了超过400次。
具体来说,Eyre-Walker 和 Keightley 对41 471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碱基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从6百万年前,也就是人类和黑猩猩分化后人类累积了143个突变,其中88个是有害突变。
Eyre-Walker 和 Keightley 直接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很难解释人类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因为人类的突变率如此之高(U>>1,每代的每个人的突变远大于1个),而繁殖率又如此之低,这对一个物种来说是很矛盾的。人类,以及人类的近亲的有害突变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这些物种的存活很成问题。”
人类基因组衰落的症状
人类基因组的衰变已经有了具体的症状。
2017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80年里,爱学习的基因衰落了。
研究者对近13万名出生在1910-1990年间的冰岛人进行了基因测序,并计算了62万个和受教育时长有关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score)。
他们发现,那些携带和更长受教育时间相关基因的人生的孩子更少,也就是说高学历基因在整个冰岛基因池中的百分比正变得越来越低。而即使是那些携带了“爱学习”基因,但事实上没有接受很长时间教育的人,生的孩子也更少。
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 Kari Stefansson 表示:“人类是因为大脑才和其他物种不一样,而教育是训练大脑的重要途径。但是和受教育年限有关的基因在基因池里却正变得越来越少。”他们还估计,平均每10年,冰岛人的IQ就会下降0.3分(IQ均值为100,大多数人的IQ在70-130之间)。
这不仅仅是冰岛一个国家的问题。早在在2016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Jonathan Beauchamp 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也指出,美国人的“爱学习”基因也在人群基因池中逐渐缓慢地消失。
其实早在2010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 Michael Lynch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里就整理了人类基因组衰退的显性证据:在美国,自闭症、男性不孕不育、哮喘、免疫系统紊乱、糖尿病等疾病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预期;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智商在过去的100年里呈缓慢下降趋势。
Lynch 认为:“现在存在大量可以减少坏基因带来的病痛的医疗技术,这就导致自然选择对有害突变松绑,”结果就是,有害突变在人类基因池中不断累积,“每代人的生理和心智机能会衰退1%。这些效应的可以预见的长期结果就是,人类的基因组衰退。”
他估计,如果没有自然选择,人类的适合度每一代下降1-3%,人类会经历生理、神经和外观上的显著失调,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国民的表型每过200-300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生理、形态、神经活动水平每200-300年就会大变样。
为什么大自然要针对人类?
有些人看到这里可能吓尿了,大自然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智人,针对智人?智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其实,这不是大自然故意针对智人,而是针对在场所有无法快速繁殖的生物。
所有无法快速繁殖的物种在演化时都会面临一大难题——霍尔丹两难(Haldane’s dilemma)。早在 DNA 测序技术发明前,生物学家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957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John Haldane)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物种要花多少代价(死掉多少个体,生出多少新个体),才能消除基因池中适应不良的那些“劣等”个体?
他先计算人工选育的情况:一个繁殖场到底要繁育多少动物,淘汰(杀掉)多少不合格的动物,才能保证能同时把拥有所有好的特质的个体都挑选出来。这样一来,繁殖场只要经过少量的几代培育,就能繁殖出一批最优秀的牲畜,不良个体不再出现,繁殖场的收益就能得到最大化。
可是,这样一波计算后,霍尔丹发现了一个令他感到十分困惑不解的矛盾。那就是,如果养的是牛,一半的母牛都不能被淘汰(在繁殖前杀掉),因为牛的繁殖率不够高,若淘汰太多母牛,最后会导致种群数量不够延续后代,更加没法人工培育优良品种了。
霍尔丹还发现,这个矛盾在自然界也适用。简单来说,如果环境发生突变,生物需要通过让不适应环境的个体死亡的方式淘汰有害基因以适应环境,那么它们反而会因此灭绝。
换言之,无法快速繁殖的生物(如人类和牛)会因为无法快速地演化而灭绝。这就是霍尔丹两难吊诡的地方。霍尔丹认为,这个两难是生物学的本质,应当成为生物学研究的重心。
霍尔丹两难后来引起了另外一个生物学大佬,日本生物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的兴趣。
1968年,他通过自己的计算,得到了更惊人的结论:“要在保持种群数量的同时把有害突变替代掉的话,每个人都要生327万个孩子才行。”因为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奇葩,他才提出了著名的中性演化理论(在分子水平上大部分突变并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自然选择对它们呈中性)。
乐观派
当然,虽然大部分科学家承认人类基因组突变量累积的事实,但是一些人对这个现象的后果却比较乐观。他们的主要观点大概是三类。
第一类观点是,人类基因组里的大部分是垃圾 DNA,它们不编码蛋白质,换句话说没什么用。这些垃圾 DNA 即使突变了,也不影响整体的功能嘛。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驳斥。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公共联合研究项目DNA元件百科全书(ENCODE)指出,人类基因组的80%都具有功能。
此外,2003年,上文提到的 Peter Keightley 和 Michael Lynch 在发表在 Evolution 上的论文中指出:“大多数突变都是有害突变,这是演化遗传学的的受到广泛承认的原理,拥有分子遗传学数据的证据基础。”
当然,也有人提出,累积太多有害突变的人要“遭天谴”,也就是说大自然会给每个人一个突变指标,如果超过这个指标,他们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活不到性成熟,找不到对象或者生不出娃什么的,所以不用担心啦。这套学说被称为突变计数理论(mutation count mechanism)。
还有一类说法是,有害突变会互相放大,导致有很多有害突变的人被早早淘汰掉,所以最终能留下来的人应该没有很多有害突变,这类理论叫做协同上位(synergistic epistasis mechanism)。
总之,下面两种假说的主要观点是,总有一天有害基因会被淘汰掉,不要担心啦。但如果这类假说是真的,那么人类总有一天会看到许多人在病痛中早死,或孤独地活着的怪现象。
原来,老师每年都说:“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这可能是真的。
本文章版权归把科学带回家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王超
下一篇:寒武纪大爆发 我们离谜底越来越近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