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x
利维坦按:
从人类短暂的文明历史来看,我们对于病毒的认知可以算是非常晚近的事了。但即便是到了今日,针对病毒是否属于生命的争论还在继续,不仅如此,对病毒稍微有些了解的人估计都会对这种肉眼不可见的诡异玩意儿怀有极为复杂的情感:尽管大多数病毒都比较友好,但总归有十分致命的……
再说个好玩的。
下图不是什么病毒,而是细菌的鞭毛。没错,如图所示,鞭毛的功能就相当于船的螺旋桨,在环境中可以高速旋转,从而推动菌体前行。
若是将细菌的内部结构放大5万倍,将发现在它旋转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类似一艘船的发动机,有着类似转动轴、推进杆等精美的机器零件。这些部件都是为了整体的功能而有序地组装在一起,每一个部件都名副其实起着应有的功能性作用,这种组合不是盲目的随机拼凑,而是一个精致的微观工程。40种各类蛋白分子机器担当了这些部件的角色,这些分子有的从环境获取能量,有的负责传感,有的如轴承一样负责转动,各司其职。这整个系统的运转,有人认为明显是一个高度智能的精致的微观工程。无法用简单的达尔文进化机制来解释。
在过去的两年里,SARS-COV2病毒,即更为人熟知的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造成了超过3.46亿人感染以及558万人死亡。百业待兴,众国封境,我们的生活被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一想到人类在这种比大多数细菌都小的病原体面前艰难作战,实在是羞愧难当。而更让人无地自容的是,这种病原体甚至可能都不是活的。
与细菌、原生动物以及真菌等其他致病因子不同,病毒处于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模糊地带,对该把它们划归为哪一边则众说纷纭。这是一场激烈而持久的辩论,并引发了一个生物学上最基本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那么,病毒是否是一种生命形式?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为了了解病毒是否是生命体,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病毒。
在人类诞生伊始,诸如天花、狂犬病、脊髓灰质炎以及流感等病毒性疾病就与我们相伴,而直到近年来,科学家们才真正了解了造成这些疾病的特定病原体。随着19世纪中叶由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人提出的微生物理论的不断发展,科学家们开始寻找并分离造成每一种已知疾病的致病原。这其中就包括了烟草花叶病,一种会阻碍烟草植物生长并导致其叶片长出斑驳的“马赛克”样图案的疾病。
在1892年,俄罗斯植物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Dmitri Ivanovsky)将被感染的烟草植物磨碎,用孔径小到无法让细菌通过的陶瓷过滤器过滤其汁液,并将过滤后的汁液接种到未染病的植物上。令他震惊的是,这些植物也难逃疾病魔爪。伊万诺夫斯基认为这一疾病可能是由某种能够透过滤网的化学毒素导致的,但是他并未进一步探索事情的原委。
马丁乌斯·拜耶林克(1851-1931)。© Wikimedia Commons
六年后,荷兰微生物学家马丁乌斯·拜耶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重复了上述实验,也证实这一令他费解的结果。不过,他对实验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在感染了一株植物之后,拜耶林克将其叶片粉碎,过滤取汁,并继续感染下一株植物,并由此循环往复。他推测,如果致病因子是毒素,那么其感染效力将随着在植物间进一步传播而降低,但是无论他传播了多少次疾病,致病效率并未稍逊半分。
起初他简单地认为该致病因子只是一个小到惊人的细菌,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地尝试,都没法让其在培养基中生长——而这是实验室中培养细菌的标准方法。而它也不受酒精的影响,后者可以杀死几乎所有已知的细菌。更奇怪的是,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致病因子似乎只在能够分裂的活细胞存在的情况下才生长和繁殖。
由于尚未弄清这是什么致病因子,拜耶林克便将其命名为“传染性活液体”(contagious living fluid),后又称之为“过滤性病毒”(filterable virus),而“virus”一词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毒素。
此后数十年,科学家使用陶瓷过滤器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病毒,他们在1898年发现了造成口蹄疫的口蹄疫病毒,在1932年发现了黄热病毒以及狂犬病毒。而理解病毒的本质则在1935年才第一次真正取得了重大突破。
温德尔·斯坦利(1904-1971)认为烟草花叶病毒是一种完全由蛋白质构成的颗粒状物质。© Sutori
当时美国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Wendell Stanley)认为烟草花叶病毒是一种完全由蛋白质构成的颗粒状物质,而非拜耶林克猜想的那种液体。斯坦利甚至还设法将病毒颗粒提纯成针状晶体,从而可以在实验室长期保存且不影响感染效力。正如1940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的那样,该发现在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温德尔·斯坦利博士制得了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晶,这让生物学家们吵得不可开交。不过也理应如此。这些晶体是活的吗?很明显它并不比钻石、玻璃、沙子以及其他我们熟悉的晶体特殊,然而把这些病毒晶体放在烟草叶上,花叶病如同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就像被活细菌感染了一般。”
斯坦利的发现让他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似乎给盛行了数世纪之久的“活力论”判了死刑,该理论认为有机体包含了某种重要本质或“神圣的光辉”,而这带来了生命。与之对比,生命化学假说则认为生命仅仅只是一个化学过程,而斯坦利发现表面惰性的蛋白颗粒可以像活的生物一样繁殖并传播,似乎也证实了这一假说。
© PLOS
然而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谜。在斯坦利有所发现的同年,电子显微镜的发明让病毒第一次可以被人类直观地观察到,也揭示了微生物学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它们。绝大多数病毒的颗粒直径在100 nm左右,是细菌直径的1/100~1/10,以致于难以通过普通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蛋白颗粒虽然具有生命力,却并不能在实验室条件下生长。
1926年,美国微生物学家托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在美国细菌学学会上做报告时提出了一种解释:
“病毒似乎是一种专性寄生物,其繁殖依赖于活细胞。”
换言之,病毒并不会像细菌、原生动物、真菌以及其他微生物一样通过细胞分裂来自行繁殖,而是通过劫持其他活细胞的分子机器来产生更多的病毒颗粒。但是病毒是如何完成这一劫持行为的呢?
事实证明,谜团的最大一块拼图仍然是缺失的。温德尔·斯坦利的后续研究揭示了烟草花叶病毒并不仅仅由蛋白质构成,实际上还包括了核糖核酸,即RNA。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科学界就遗传特征如何于生物体中实现代际传递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尽管遗传定律在19世纪60年代就被捷克神父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发现,并在20世纪初被美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以及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所完善,但是编码以及传递特定遗传信息的具体分子并未揭开其面纱。
一些科学家猜测RNA以及其兄弟DNA等分子可能是遗传物质,然而大多数人认为遗传物质更可能是蛋白质,因为后者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因此可以储存更多的遗传信息。而病毒在判定何种假说是正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3年,玛莎·蔡斯(左)与艾尔弗雷德·赫尔希。© PaulingBlog/Karl Maramorosch
1952年,美国细菌学家艾尔弗雷德·赫尔希(Alfred Hershey)和玛莎·蔡斯(Martha Chase)利用能够感染大肠杆菌的病毒——T2噬菌体开展了一系列现在被认为是经典之作的实验。当时的科学家已知该病毒会将自己体内的一部分物质注射入宿主细胞,并把其余部分留在体外。
但问题是:被注射的部分是核酸还是蛋白质呢?
为了找到答案,赫尔希和蔡斯用放射性硫标记了一种细胞培养基,这使得这批病毒中只有蛋白质会具有放射性标记。而另一批病毒则在存在放射性磷的环境中被培养,这使得这批病毒中只有核酸部分被标记。两批病毒接下来分别感染未被标记的大肠杆菌。研究人员通过离心机将后续培养液离心,分离被感染的细菌以及病毒被丢弃的非编码部分。
当两位科学家检测被感染细胞的放射性时,他们发现那些磷被标记的实验组中的细菌具有放射性,而硫被标记的实验组则没有放射性。这也证实了病毒注入细菌体内的是核酸而不是蛋白质。之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以及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等科学家解释了DNA和RNA的结构与功能,从而开启了一场如今仍在影响世界的基因革命。
冠状病毒(SARS-CoV-2)结构的计算机模拟图。© Janet Iwasa/University of Utah
今天,人们都了解到所有病毒都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段类似于DNA或RNA的序列,以及蛋白质外壳或衣壳——或者正如英国生物学家彼得·梅达瓦爵士(Sir Peter Medawar)简洁易懂的描述:
“(病毒)就是一段坏的信息被包裹在蛋白质中。”
病毒的形态与尺寸千变万化,从直径约27 nm的猪圆环病毒到长约1.5 μm的阔口罐病毒;从长管状的烟草花叶病毒到球状的冠状病毒。除了蛋白质外壳,很多病毒还含有从宿主细胞上获得的脂质包膜。病毒的生命周期起始于它们进入宿主细胞,与其细胞膜相互接触的那一刻。如果某细胞是该病毒的易感细胞,病毒就会附着在其表面,像微型注射器一样将遗传物质以及一些酶注入细胞的胞质中,并留下其衣壳。
一旦进入细胞,病毒的遗传物质就开始露出邪恶的獠牙,劫持细胞的代谢机制,将其从独立的有机体转化为小型生物工厂,这个工厂只有一个目的:产生更多的病毒颗粒。病毒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劫持过程。
冠状病毒与细胞的融合方式动画演示。© Janet Iwasa/University of Utah
对于DNA病毒,它的遗传物质会取代细胞自己的DNA,并利用细胞自己的酶将入侵基因组转录为信使RNA,即mRNA。该mRNA随即被称为核糖体的细胞器读取,后者利用读取的遗传指令将氨基酸组装成蛋白质。核糖体不再生产用于维持细胞正常运转的常规蛋白质,成为了新病毒的“始作俑者”。而RNA病毒则包含了可以直接被核糖体读取的mRNA,可以完全跳过DNA转录的步骤。
此外,还有一种反转录病毒,它拥有更精妙的遗传技巧。包括HIV在内的反转录病毒含有一种特殊的酶——反转录酶,它能将病毒的RNA整合到宿主细胞自身的DNA中。这种嵌入的病毒基因组被称为原病毒,它能在宿主的基因组中休眠很长一段时间,避开免疫系统的监控,神不知鬼不觉地随着细胞的分裂和繁殖在细胞间传播。它们还能自发激活,使得细胞开始再次生产病毒。这使得人们对反转录病毒的感染束手无策。
皮疹是HIV感染的常见症状。© WebMD
但是反转录病毒对人类的重要性远超造成的疾病所带来的影响。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足足有8%的人类基因是从原病毒中获得的。显而易见,这些基因搭便车者对地球上生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影响。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093845/)
一旦新的病毒颗粒组装完成,它们接下来必须离开宿主细胞。感染细菌或其他单细胞有机体的多种病毒会通过裂解周期完成这一目的。在这一过程中,细胞膜会破裂或溶解,宿主细胞死亡并将新一代病毒释放到环境中。
然而,病毒如果杀死遇到的细胞,就会迅速导致宿主以及寄居其中的病毒的死亡,所以大多数病毒会通过胞吐或“出芽”的方式离开细胞,在不破坏细胞膜的情况下穿过它。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最终都殊途同归:新组装的病毒被释放到环境中,摩拳擦掌来感染新的细胞并重新开始这一过程。
﹡﹡﹡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病毒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繁殖的,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病毒真的是活着的吗?
如同生物学中很多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如何准确地定义生命。生物学家对于他们实际研究的东西并未形成共识,这在整个科学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乍一看,某物是否有生命的问题看起来非常直观。
然而纵览历史长河,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对生命给出严谨且可以验证的定义。我们所能达到的共识基本上可以浓缩为“眼见为实”。但是缺乏这一定义并不妨碍生物学家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多年来关于定义的探讨也仅仅停留于哲学上的好奇。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索宇宙并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时,“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便突然变得重要。
© Baamboozle
多年来,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一直在试图描绘出生命体所具有的独特性质的清单,以下便是其中一个来源于NASA网站的报道:
“【生命体】拥有从环境中获得能量的能力并将其转化用于自身的生长和繁殖。生命体趋于内稳态:在定义其内部环境的众多元素上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生命体能够(针对环境)做出响应,通过刺激产生类似于反应的动作,如回缩,甚至如学习等更高级的形式。生命体具有繁殖性,因为种群的突变以及自然选择,生命体的进化需要一定程度的复制。为了生存和发展,生命体需要首先成为‘消费者’,从而交换生物质,创造新的个体以及排泄废物。”
然而,很多非生命系统也会表现出很多上述性质。比如说,晶体可以自发组装成令人惊异的复杂且有序的形状,进行自我复制,将同一内部结构在晶体间进行转移,甚至会移动来响应外界的刺激。同样,一块黑色的石头也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并通过加热周围的空气转化为动能,同时其中放射性的组分也会自发地将核能转化为热能。
《星际迷航》中以岩石为生的霍塔(Horta)。© Tumblr
前述定义在应用到生物界时,甚至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比如朊病毒是牛海绵状脑病(该疾病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疯牛病)的致病因子——它比普通病毒甚至更简单,仅由一段错误折叠的蛋白构成,并不包含任何遗传物质。然而,朊病毒可以变异,可以在物种间传播、繁殖——虽然不是通过遗传信息,而是通过造成临近蛋白的错误折叠引发致命的连锁反应。
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而那位以提出将假想的猫放入假想的箱子中而闻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则提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生命体所独有的性质。在他出版于1944年名为《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中,薛定谔如是称述:
“有机体具有自我控制‘秩序流’的惊人禀赋,因此能够避免使原子衰变入混乱境地。”
换句话说,生命体似乎会违背第二热力学定律,该定律认为在封闭系统中,熵——被不同的方式定义为无序状态或一种不能用于做有用功的能量——一直是增加的状态。在不断趋于无序的自然力量面前,生物体不仅设法保持了高度的内部秩序和复杂性,而且在数代中保持该秩序,并几乎不损失保真度。
埃博拉病毒。©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当然,生命体并未真正违反第二定律,因为它们并不是封闭系统。它们是半封闭系统,一方面足够封闭,能够维持内部秩序,另一方面又足够开放,确保体内秩序的增加会被外界环境中秩序的降低所抵消——比如通过排出多余的热量(来降低生命体内部的熵值,增加环境熵值)。然而,这些观察让薛定谔推测半封闭结构对于生命体功能的实现非常关键。
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推测,为了准确将它们的内部结构以及复杂性传递给后代,生命体需要构建包含某种形式的“代码脚本”,并在其中囊括构建这一特定生命体的指令。后来,这一有先见之明的预言不到十年就随着DNA结构与功能的确证而被应验。
单纯疱疹病毒第1型(HSV-1)。©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紧随薛定谔之后,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Smith)认为生命的本质属性是其能经得起达尔文式自然选择的考验,那些能够增加有机体繁殖能力的遗传特征被优先选择并被传递给后代,确保物种能够随时间不断演化。最终这一概念与之前的定义相结合,产生了所谓的“NASA生命定义”,它指的是:
“生命是一种可以适应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且能实现自我可持续的化学系统。”
对于生命定义中适应进化的观点,病毒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新冠病毒已经快速变异、产生了多种变种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病毒是生命体”这一观点在定义的第一点上却是充满争议的。不像其他生命体,病毒无法在缺少其他活细胞的情况下繁殖。如果不能劫持宿主细胞的分子机制,病毒仅仅只是一团惰性的蛋白质以及遗传物质。因此,索尔克研究所的杰拉德·乔伊斯(Gerald Joyce)认为:
“根据这一基础定义,病毒并不符合标准。”
不论是否能被归为生命体,显而易见,病毒都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无法精准测定,生物学家估计全球约有10^31种病毒,如果把所有的病毒一个挨一个连接起来,将延伸至2亿光年之外,这一数字使人大跌眼镜——远远超过了已知最远的星系。在地球上所有的环境中,我们都能觅得病毒的踪迹,它们能感染所有已知的生物体。尽管绝大多数病毒都比较友好,不会造成恶性疾病。
© BioCosmos Africa
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对地球上生命的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它们会通过反转录的方式将病毒基因插入宿主的DNA中。比如血橙的存在就应该感谢名为Tcs2的病毒基因,后者会响应寒冷的气候并转变为名为Ruby的基因,这就赋予了果肉独一无二的深红色调。
与我们人类关系更紧密的是一种名为ERVW-1的古老基因,它是人类胎盘中融合细胞结构,即合胞滋养层(syncytiotrophoblast)的形成原因,该结构对营养物质向发育中的胚胎转移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都要归功于数百万年前感染非洲人猿的一种病毒。
© Timo Lenzen
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科学家认为NASA对于生命的定义过于狭隘,应该有所拓展,并将病毒这样边缘性的案例囊括其中。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帕特里克·福泰尔(Patrick Forterre)便是其中一员,他认为:
“生命以及生命过程只是对我们星球上目前有的物质复杂进化形式的一些称呼。”
福泰尔认为病毒并不仅仅是蛋白质以及核酸的集合,更是一种在生命循环过程中拥有两种不同状态的有机体:病毒颗粒,以及“病毒细胞”(virocell),即被病毒颗粒攻占并转化为产生更多病毒粒子的活细胞。在福泰尔的理论中,病毒细胞与正常健康形态下的宿主细胞——“核态细胞”(ribocell)截然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
“正常细胞的梦想是分裂以产生两个细胞,而病毒细胞的梦想是产生100个甚至更多的病毒细胞。”
因此,根据福泰尔的理论,病毒颗粒之于病毒细胞犹如种子之于橡树。病毒与其他任何寄生物没有任何不同,都是依赖寄主细胞生长和繁殖。而病毒仅仅只是依赖程度更甚。
另一些科学家认为任何对生命进行严格定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这将阻碍我们在地球或其他星球上去认识尚未发现的奇异的生命形式。正如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哲学家卡罗尔·克莱兰德(Carol Cleland)所言:
“定义只是通过我们的语言告诉了我们某个词语的含义,但是并未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在生命这个案例中,科学家感兴趣的是生命的本质而非‘生命’这个词在我们语言中的含义。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是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生命系统理论,而不是对‘生命’一词的精准定义。”
尽管形态千变万化,地球上的生命却只代表了一方面。形成生命系统的普适理论的关键便是探索生命的其他可能性。我感兴趣的是制定一种寻找外星生命的策略,让人们能够拓展我们以地球为中心的生命概念的边界。
© Shira Inbar
另一方面,我认为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定义“生命”也是件徒劳的事,因为这并不能告诉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什么是生命”。关于生命的科学理论将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解答这些问题,并且对于一些【边缘性的案例也能奏效】。仅仅为了某些人的一己之欢而将非典型的“生命体”纳入“生命”范畴,这对生命科学的发展毫无裨益。”
争论愈演愈烈,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家都坚信这一问题都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了。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考虑到它们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对于地球生命的影响,不论病毒是否是生命体,它们都值得我们无上的钦佩与尊敬。
文/Gilles Messier
译/药师
校对/Yord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2/06/are-viruses-actually-alive/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药师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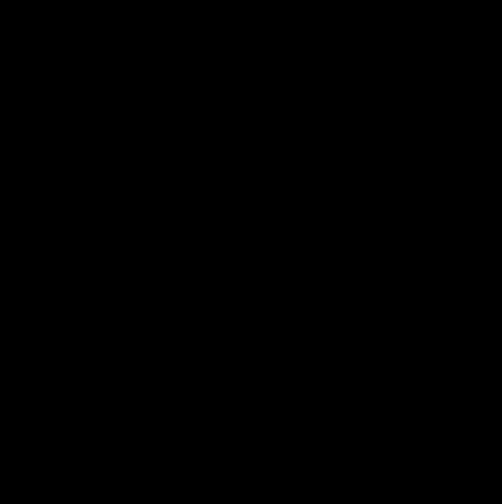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