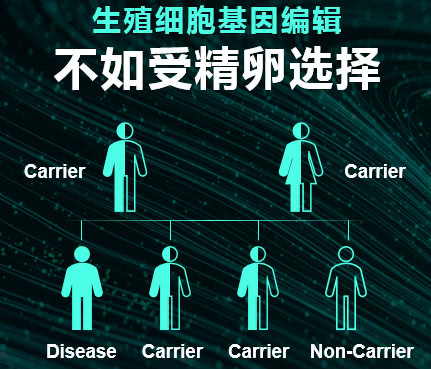2019年1月15日晚,由知识分子、赛先生和科技日报共同发起的 “科学精神中国行”新年讲演专场活动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该活动由知识分子、赛先生和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联合主办,旨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最新科学思想,构建中国的新型科学文化。作为整个系列活动的首场,当晚,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为大家作了题为“基因编辑与人类未来”的演讲。饶教授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出发,探讨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本文由“腾讯科学”根据报告内容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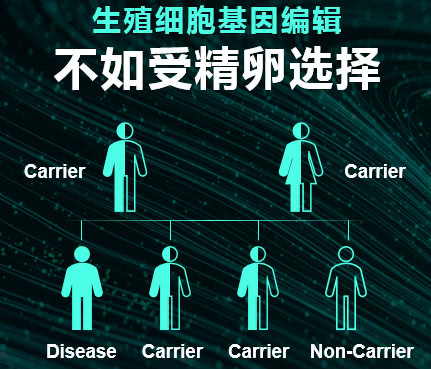

2019年1月15日晚,由知识分子、赛先生和科技日报共同发起的 “科学精神中国行”新年讲演专场活动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该活动由知识分子、赛先生和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联合主办,旨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最新科学思想,构建中国的新型科学文化。作为整个系列活动的首场,当晚,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为大家作了题为“基因编辑与人类未来”的演讲。饶教授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出发,探讨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本文由“腾讯科学”根据报告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