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文化的讨论中,自然科学界的工作者应当能够充分了解自然科学自身走过的历程,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复杂面向(不再坚持“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特别是感受到高科技是风险社会中风险的重要来源,从而主动担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撰文 |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石丛书”持续25年,到2023年已经出版153种。也就是说它坚持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变化速度非常快的现代中国,有哪些事能坚持这么久?真的不多。
就出版而言,我立即想到国外的两套丛书。其一是斯普林格出版社的“GTM丛书”(“研究生数学丛书”),到其最近出版的《自守表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Automorphic Representations)一书面世,该丛书已经出版了300种。此丛书在中国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的影印本封面一律为黄皮,殊为简易,与其相对艰深的内容形成颇好的对照。其二是柯林斯出版社的“新博物人丛书”(New Naturalist),从1945年的第一种《蝴蝶》到最近《池塘、水池与水坑》(Ponds, Pools and Puddles)共计148种,78年来平均一年出版不到两种。此丛书封面设计极为讲究,美丽大方,令人爱不释手。“哲人石丛书”就规模、形式、题材等方面看,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国内诸多人认为“哲人石丛书”是科普或者高级科普。这种概括就其中的个别图书而言说得过去,但整体而论则不符,因为“科普”两字无法罩得住如此广泛的内容,恐怕还是叫“科学文化”比较合适。不管如何归类,此丛书能够坚持下来,都是一个奇迹。它对中国科学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会一点一点显示出来,不需要着急。
举个很小的例子,《大流感:致命瘟疫的史诗》最早出版是2009年,但是在2020年初疫情开始以后,它成了无数人推荐的必读书,因为它不只是简单讲述1918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一部与流行病有关的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都是如此,《确定性的终结》《数学大师》《改变世界的方程》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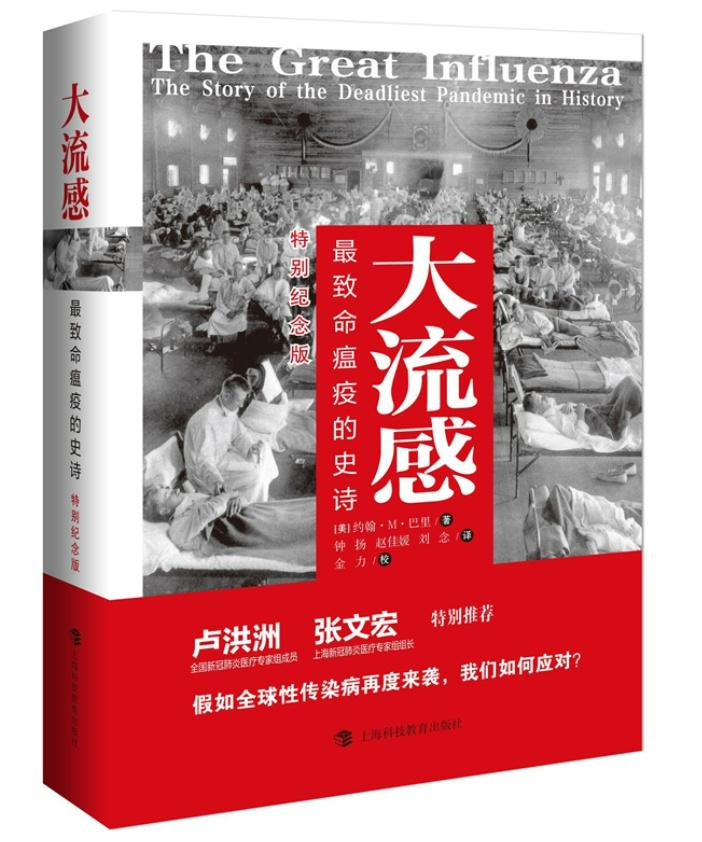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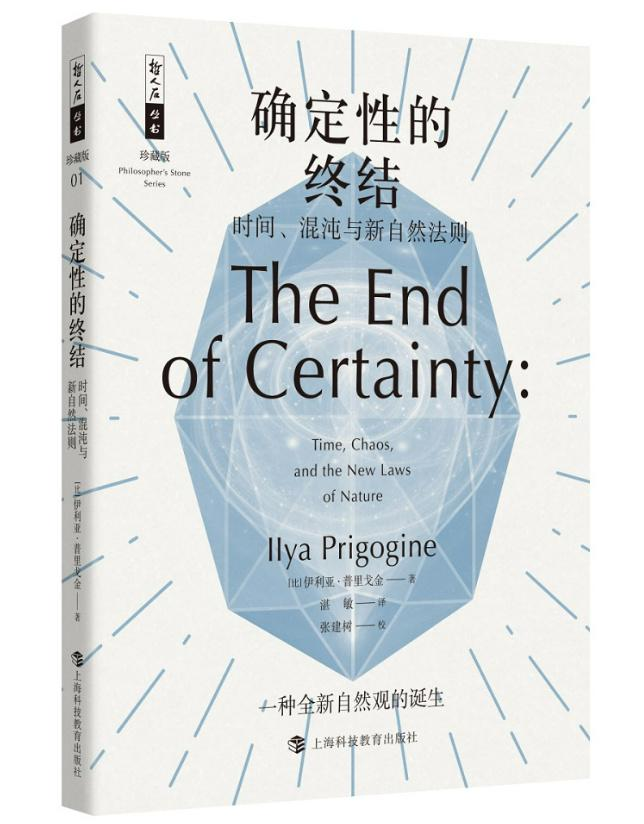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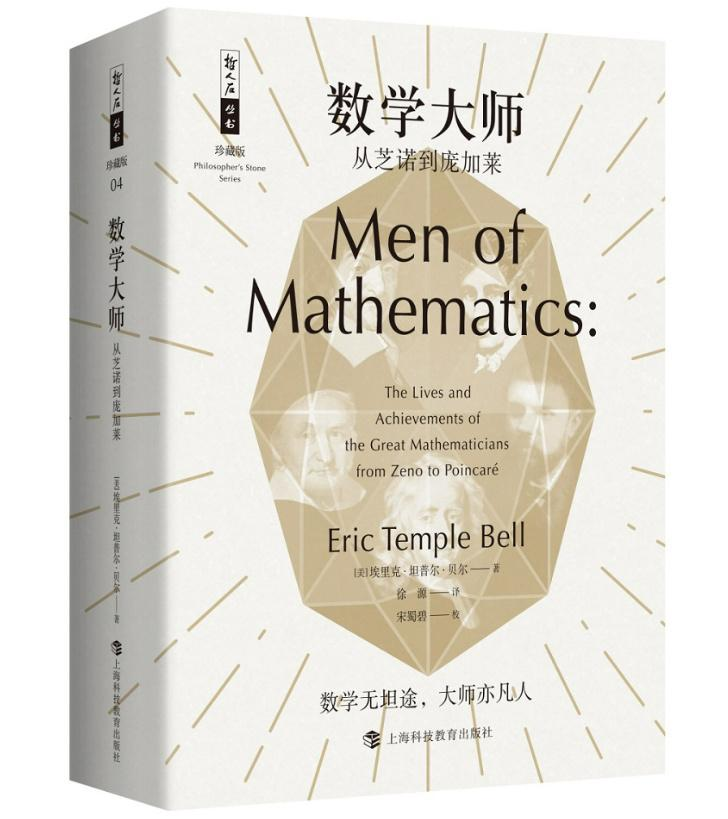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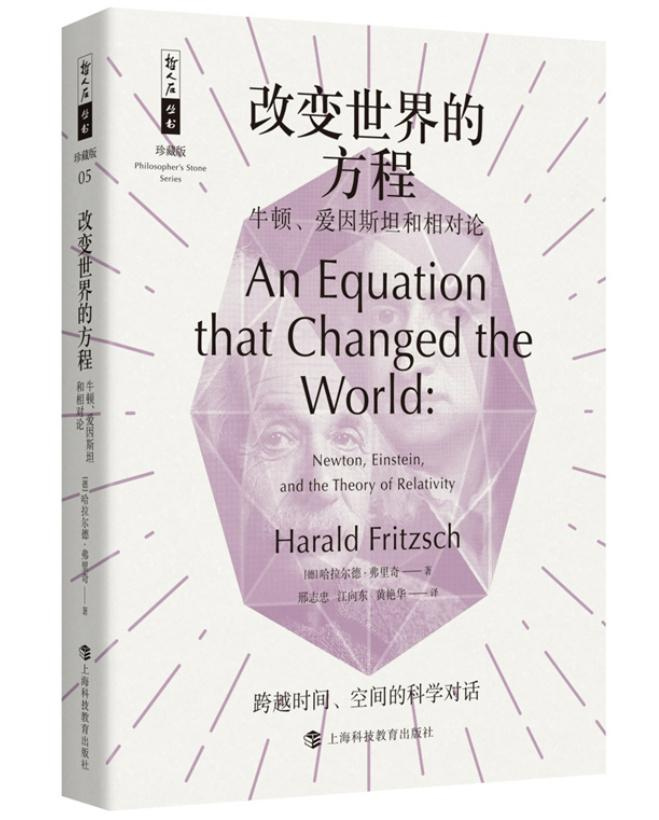
2023年11月12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五层“文会堂”举办庆祝活动,后来该社总编辑王世平来信,提及当日座谈会时间太紧,“你只说了几句话,不过瘾啊”,嘱我写篇文章。那天我讲了两件事,但没有展开。
第一件事是,“哲人石丛书”出版质量非常高,可以说在中国树立了一个标杆,但是其宣传、发行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多年前潘涛、刘兵曾示我一份调查报告,提及想象中的科学家读者并不是此丛书的主要读者。实际上,中国当今一线的科学家主要读论文,而不读书!这令人吃惊吗?惊也不惊。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科学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就基础性研究的重大创新而言,还差得远。既然不是经费问题也不是智商问题,那究竟是为什么?讨论已经很多,有人说中国科学家热心追赶式模仿式研究太多,自由精神不足,也有人说是文化储备不够,总之没有把握住自然科学创新的精髓。按理说,缺什么补什么才对,但现实正好相反。科学家不读也没关系,如果年轻人读,将来他们长大,成为科学家,在其研究中也就能有所体现了。就像《引力世纪》《自然的悖论》《脑壳里的互联网》分别在物理学、生物学、脑科学这样的基础学科里写出了创新性的内容,当今天读这些书的年轻人成为未来的科学家,他们的视界将有很大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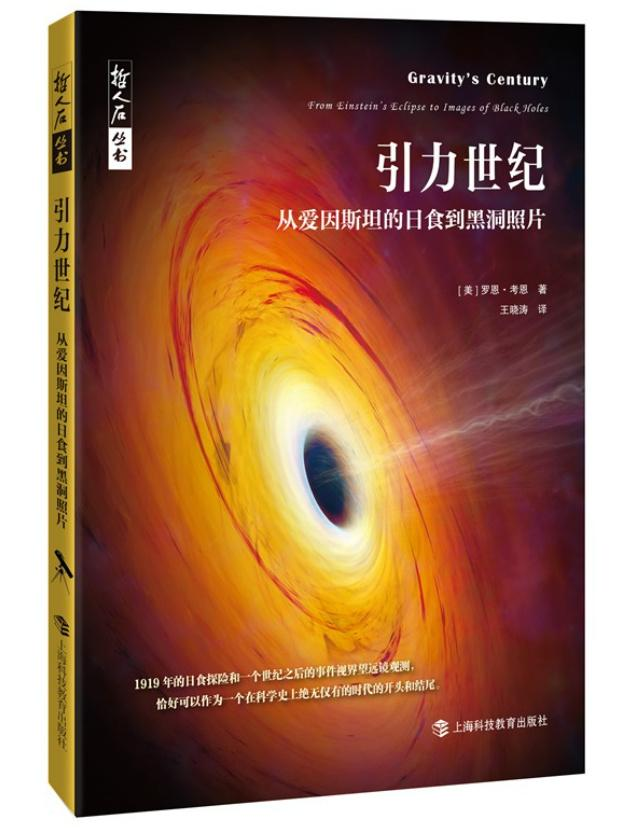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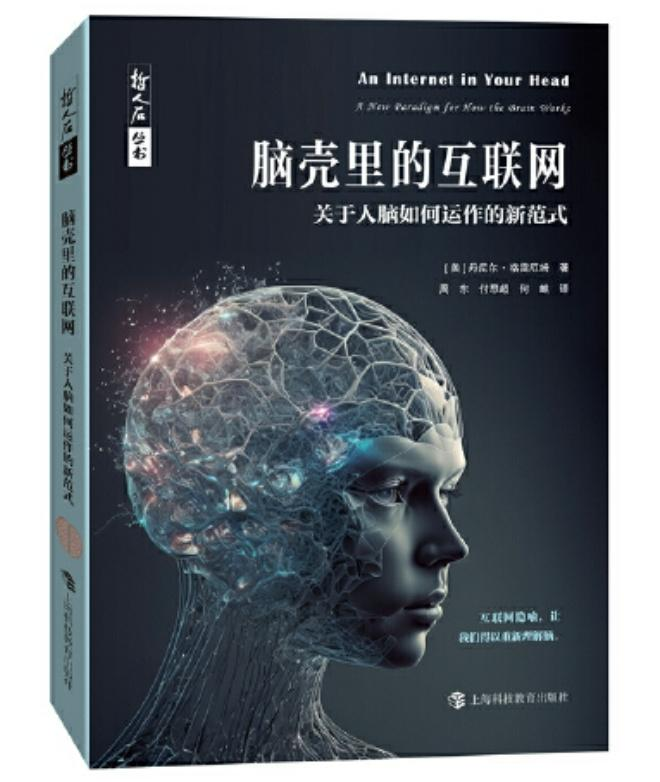
但这并非我说的要点,这只是引子,提一下就是了。我的建议是对“哲人石丛书”进行二次开发!道理是,相对于中国读者的文化素养、科学素养,这些书还是偏难了。直接阅读“哲人石丛书”,相当一部分人还有困难。这就需要做化简,需要有人对图书进行解说。现在,社会中恰好有许多公司在做这类工作。据我了解,当下的情况是对经典电影、人文社科图书,解说工作做得相对好,对数学、自然科学类图书所做解说工作反而少。这无疑值得大力开发。吴国盛教授组织高山科学经典阅读,每本书都请专家来解读,此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可以借鉴。在我的印象里,《确定性的终结》《我思故我笑》《素数之恋》《隐秩序》都是非常值得解说的经典书。《素数之恋》有读者称之为最棒的数学科普书籍,将数学史和数学知识结合得极其精彩,如果能有人将数学知识部分给读者再解读清楚,相信这本书的影响力还要扩大一个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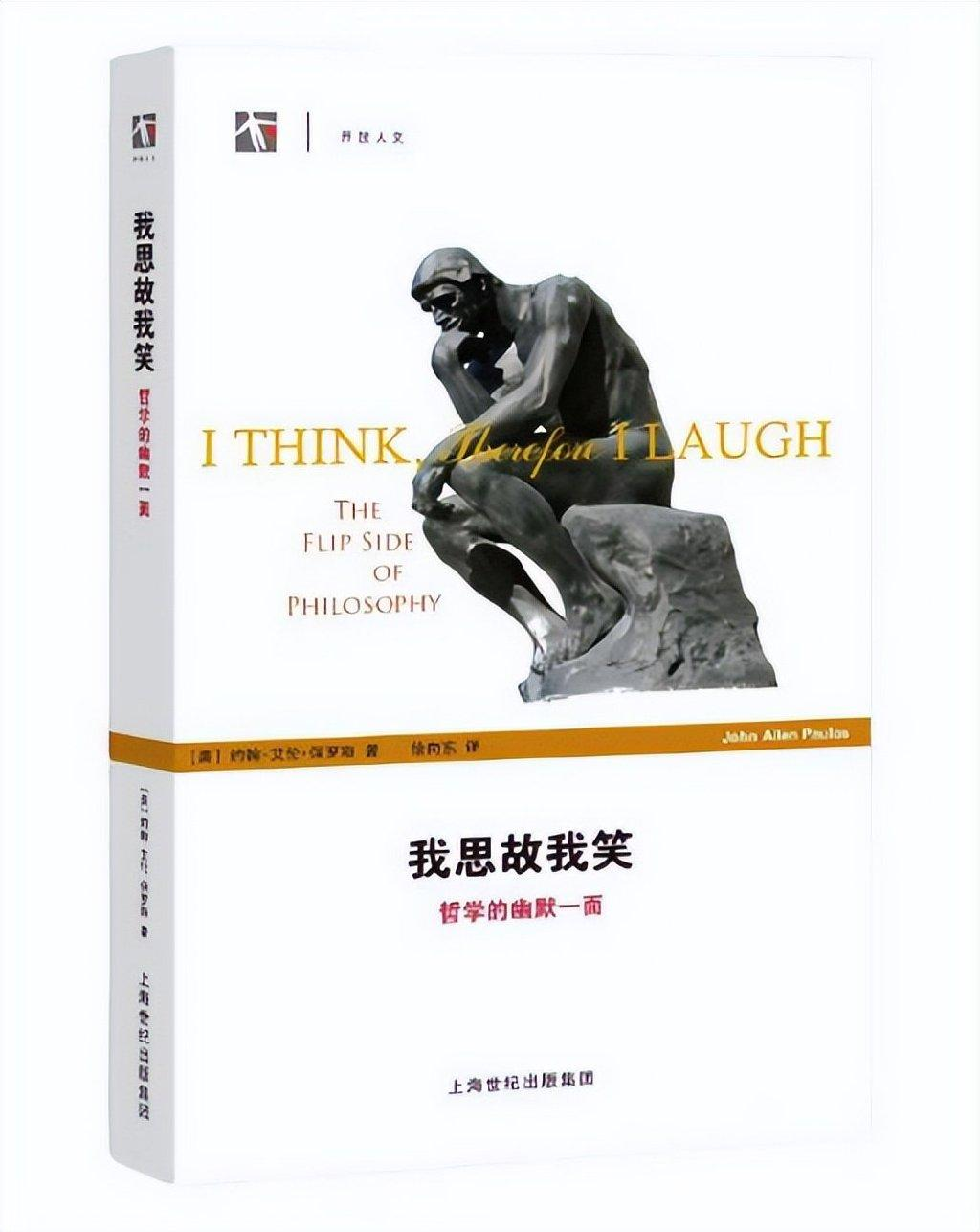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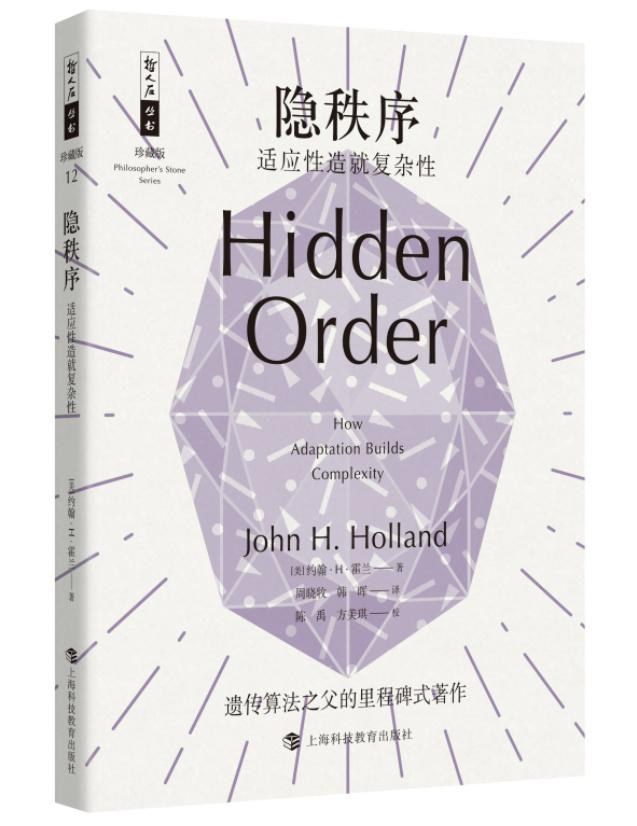
谁来二次开发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人手有限,编辑们的长处是编书,而不是直接面向公众宣传、解读图书。图书作为商品,是很难通过打广告来营销的,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产品。这跟卖萝卜、卖电视、卖化妆品、卖手机有很大不同,萝卜、电视、化妆品、手机虽然每一批次也不同但各自都是一类东西,区别只在于质量、性能和品牌,而图书则几乎本本不同,由一本书无法猜测到另一本书在讲什么。出版社应当把二次开发的工作外包出去,让专业公司来做,收益按比例分成,自己仍然继续做“哲人石”的编辑出版工作。现在社会中存在许多未授权的解说、营销活动,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实际上侵害出版社的利益。与其如此,不如正式一点,一部书只向某一两家公司或个人授权;非授权的营销皆为非法,可以要求取消、下架。这样出版社能够在有收益的情况下继续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关于科学文化评论。不是已有的《科学文化评论》那种性质的评论。当天的庆祝会上,韩启德先生、邬书林先生、周忠和先生的发言都非常真诚、实事求是,信息量很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就斗胆讲了自己的想法。我说关于科学事务,正常评论、批评的渠道还不够畅通。这可能部分受了田松讽刺性地概括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之影响。如果这般荒唐的归类成立,科学在整体上就将免于“证伪”,那是相当奇怪的事情。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概括科学的核心特征是“可证伪性”。但那是就具体的命题、猜想、理论而言的,而非就整体性的科学事业而言的。在现实中,科学界内部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实可以正常开展批评,科学有自己纠错的本事,因而科学生机勃勃,不断生产出靠谱的新知识。但是,当科学面对其他文化时,科学的保守性显示出来了,在现代社会,人们没有办法事先描述出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将放弃科学,这相当于科学无法被证伪。想一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似乎都得相信科学,无论出现何种经验事实。这样的现象当然不限于科学,宗教和教条也如此,对于其信仰者,经验具有不可入性,不可能证伪其信念。但这对于百姓日常生活、对于天人系统可持续发展,却是相当糟糕的事情,因为风险增加了。自然科学有其长处,它强调客观性、确定性、定量化,就不得不对现实系统进行高度化简,不得不在小尺度上运行(相对于各自系统的本征尺度而言,比较绝对值没有意义),因此失真和短期化是其制度性要求,是它本身无法克服的。
有人说,科学界对此早有认知,也在试图改进,比如现在有“复杂性科学”,没错,但是瞧一瞧轰轰烈烈的“复杂性科学”的艰难历程就明白了,“哲人石丛书”从2000年就出版了讲“复杂性科学”的《隐秩序》,后来还出版过《混沌与秩序》《混沌七鉴》和《解困之道》,尽管都是好书,《隐秩序》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经典之作,《解困之道》在国内获奖无数,但影响力始终有限:自然科学真的是化繁复为简约,而不是相反;反过来做,不是科学的强项,做来做去“复杂性科学”始终成不了科学的主流。这就意味着,从长远看,需要用科学之外的东西来平衡科学。这种东西或多种东西要足够强大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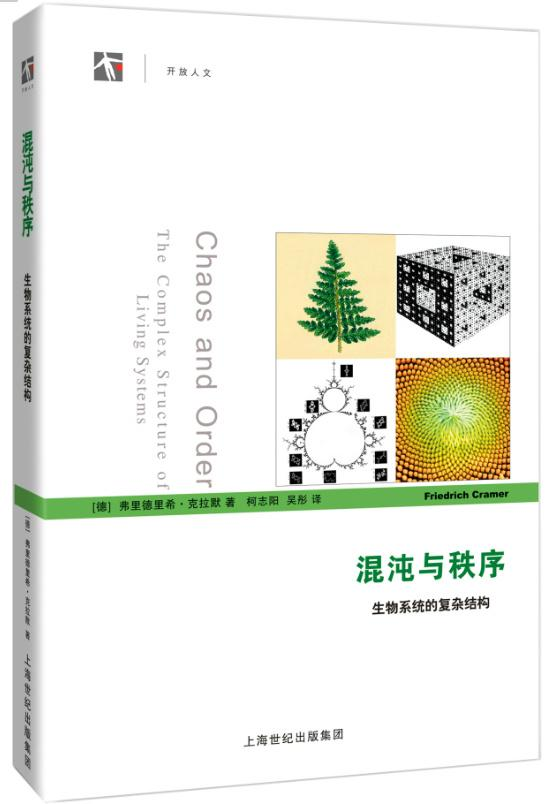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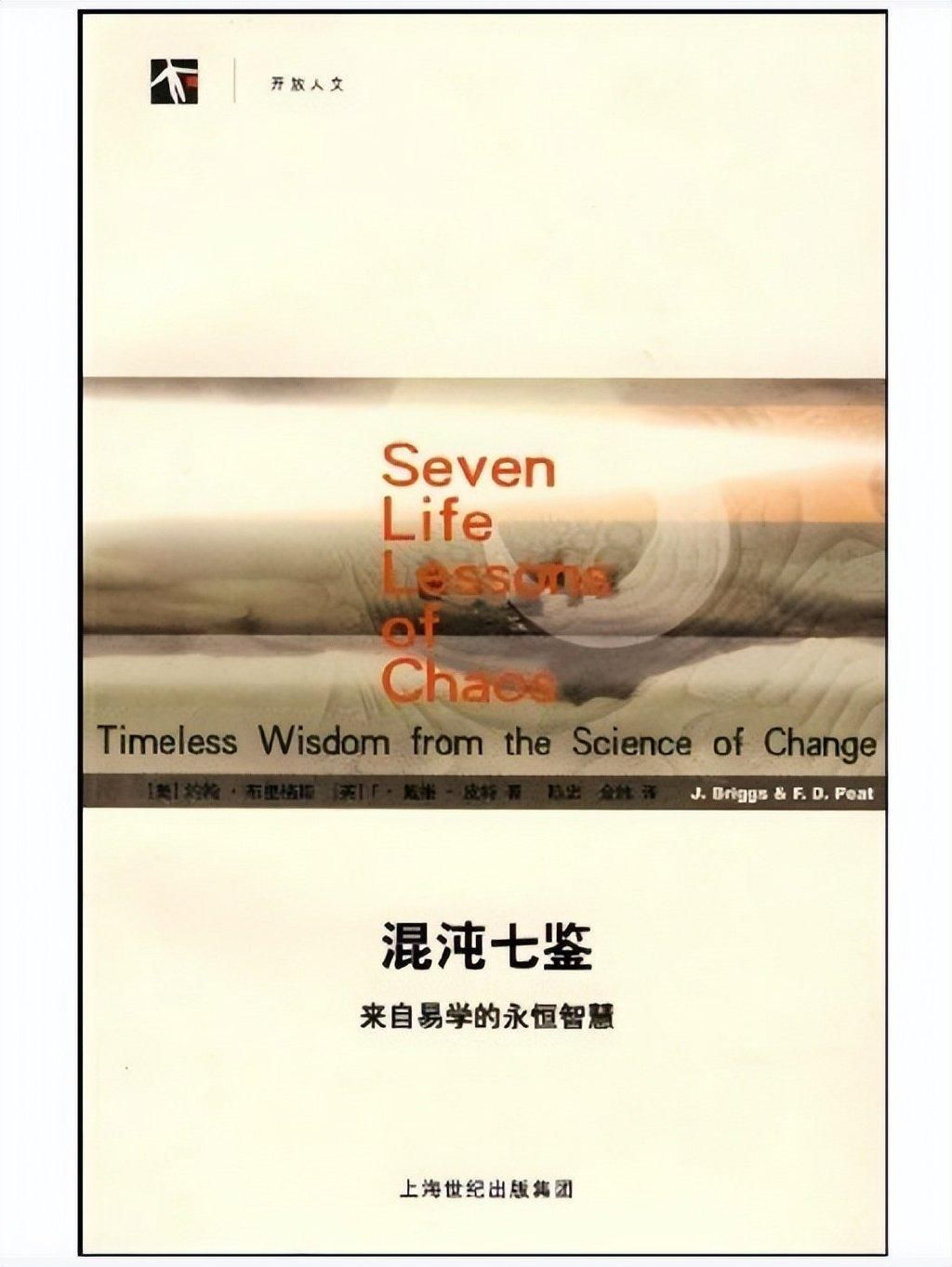

有这种东西吗?我认为是有的。在文艺界早就有“文艺批评”,从来没有人说它反文艺。相应地,也可以憧憬一种“科学批评”领域和行为。这不是反科学,它是克服现代性危机所要求的理性行动。要建立这样的领域、鼓励这样的行为,丰富科学文化是首先要做的,毕竟大家要有一定的对话基础。在科学文化讨论中,自然科学界的工作者应当能够充分了解自然科学自身走过的历程,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复杂面向(不再坚持“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特别是感受到高科技是风险社会中风险的重要来源,从而主动担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
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监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特 别 提 示
1. 进入『返朴』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精品专栏“,可查阅不同主题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朴』提供按月检索文章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类推。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摘编。转载授权请在「返朴」微信公众号内联系后台。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