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尼警方通报了一起骇人的盗猎事件:自2018年至今,14名盗猎分子共射杀了26头爪哇犀牛(Rhinoceros sondaicus)。
爪哇犀是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现存种群规模估计为76~82头。换言之,这些盗猎分子猎杀了世界上1/3的爪哇犀。
印尼爪哇岛的乌戎库隆国家公园是爪哇犀现存的唯一栖息地。爪哇犀栖身密林又性情谨慎,人们难以实时监测它们的生存状况。在过去十几年,印尼官方只能通过公园内的120台红外相机,对爪哇犀进行个体识别,才初步统计出了它们的现存种群规模。
然而,在这约80头爪哇犀中,有至少15头在过去3年中都没再被拍摄到,这令印尼官方开始警惕犀牛非自然死亡的可能。
生活在乌戎库隆的爪哇犀|Alain Compost / savetherhino.org
从去年11月开始,当地警方抓获盗猎分子。其中一个10人的盗猎团伙供认,他们至少猎杀了22头爪哇犀;另一个4人团伙则至少猎获了4头。
盗猎分子不仅长期非法进入乌戎库隆实地勘察,而且借助网上的旅拍视频等掌握公园内信息,甚至还摸清了几部红外相机的位置,利用官方保护犀牛的设备搜寻犀牛踪迹。他们用土制猎枪射杀犀牛,就地切割犀角,再通过中间人介绍将犀角走私到中国,目前印尼警方已经锁定了两名中国买家身份。
虽然在这5年里也有犀牛幼崽诞生,爪哇犀种群应当有动态恢复,但它们的繁殖效率并不高,5年内猎杀高达1/3的个体足以对爪哇犀种群构成致命性打击。
和火山与时间赛跑的保育工作
爪哇犀过去曾广泛分布于印度东部、中南半岛各国、我国西南部和印尼群岛。这一物种包括三个亚种,但随着着栖息地的破坏和过度猎杀,印度亚种(R. s. inermis)已于上世纪初灭绝,越南亚种(R. s. annamiticus)也随着最后一头雌性个体于2009年被猎杀而宣告灭绝。此后,印尼爪哇岛上的乌戎库隆国家公园成为爪哇犀的最后栖息地。
最后一头爪哇犀越南亚种的尸骸,及其骸骨上残留的弹片|WWF
然而,乌戎库隆国家公园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伊甸园”。
乌戎库隆位于爪哇岛最西端的狭小半岛上,其正北侧60公里处即为著名的喀拉喀托火山。1883年,火山猛烈喷发引发海啸,不仅夺走了3.6万人的生命,还彻底摧毁了乌戎库隆半岛的生态。火山喷发崩解后形成的新火山如今也异常活跃,最近几年都有较强烈喷发。我们无法推测它何时会再次引发区域性的生态灾难,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印尼的爪哇犀保育工作,几乎就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时间游戏。
去年6月再度喷发|Indonesia's Center for Volcanology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Mitigation Agency
按照印尼政府和国际保育组织的规划,爪哇犀的保育会首先确保乌戎库隆的种群平稳恢复,再选择健康成年个体异地重建“备份种群”。然而,印尼的爪哇犀恢复工作自始就困难重重。1883年的火山喷发已将原本的种群抹杀殆尽,今天生活在此的爪哇犀是后来少数重新迁入的犀牛个体的后代,因而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本身并不高。爪哇岛亦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挤压下,适宜爪哇犀生活的区域仅为3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相当大面积还受到外来物种砂糖椰子(Arenga pinnata)的入侵。
1967年,印尼对公园内的爪哇犀进行初步统计,只发现了25~30头爪哇犀。此后虽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但种群在80年代增长到50~60头后,恢复速度明显减缓,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很可能是由于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很难再支撑更多犀牛生活于此。
为破解这一困境,保育人员将栖息地的恢复作为重中之重。在国际资金资助下,印尼官方雇佣周边社区居民清理被砂糖椰子入侵的林地,补种原生植被,以拓展适宜犀牛栖息的生境。周边居民通过参与森林恢复工作获得收入,自然也消解了砍伐原生林开荒的积极性。仅在最近十余年,乌戎库隆就恢复了5000公顷的原生林地,红外相机里不断出现的犀牛幼崽也侧证了栖息地恢复的成效。
2020年,印尼官方公布的国家公园内的爪哇犀幼崽图片|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
乐观情绪渲染下,已有保育学者开始畅想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另寻他处,重建一片至少4000公顷的栖息地;从乌戎库隆选择体格强壮、正处于繁殖阶段的5雄3雌作为迁地保护的“火种”。他们猜想,在未来20年内,爪哇犀的种群规模或许可以恢复到150+头,逐渐摆脱灭绝的厄运。
但就在此时,盗猎的枪声骤然响起……
被忽略的盗猎
为何印尼的爪哇犀保育工作屡有突破,却对时间跨度如此之久、猎杀规模如此之大的盗猎行为毫无察觉?
尽管犀牛受到多份国际公约的保护,但在全球尺度下,针对犀牛的盗猎规模却并未明显衰减。尤其是在南非、纳米比亚等犀牛栖息国,盗猎依然是影响犀牛种群恢复的主要因素,仅2023年在南非就有499头南白犀被盗猎。盗猎导致自2017年以来,全球5种犀牛的总规模缩减了3.7%。
被盗猎的南白犀|savetherhino.org
万幸的是,针对印尼的两种犀牛——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的盗猎新闻却很少出现,上一次针对爪哇犀的盗猎还要追溯到1998年。有乐观的声音认为,这是印尼保护得力的表现。印尼对爪哇犀的保护工作确实颇为全面,除了对乌戎库隆的陆上区域进行巡视之外,还有海上巡逻队专门防范盗猎者从海路非法入侵;外界通往乌戎库隆的道路也早在国家公园设立之初就被切断。长达20年的风平浪静或许也让保育人员相信,盗猎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然而,站在今天回溯,关于爪哇犀的盗猎活动多年未再出现,其实或许只是个概率学上的侥幸。爪哇犀种群规模极小,行踪又远比非洲近亲更难搜寻,其低矮的独角也不如白犀、黑犀角更容易换取暴利,自然无法吸引国际性的盗猎网络关注;加上当地较高频率的巡护力度,盗猎爪哇犀的性价比并不高。但当本地盗猎团伙掌握了翻查红外相机寻找犀牛的技巧,同时恰逢COVID-19大流行限制了日常巡护,盗猎的风险收益比也在悄然逆转。
被盗猎者杀害并割角的黑犀牛|the Lewa Conservancy
当然,巨额收益永远是盗猎的核心动机,其背后则是犀牛非法贸易的旺盛需求。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犀角非法贸易的核心市场之一。和象牙不同,犀角除了被作为工艺品之外,人们对其“医用”的需求更为旺盛,而且犀牛角的“药效”已经从传统的祛热,与时俱进地演进到了“抗癌”——哪怕这些“药效”都是子虚乌有,犀牛角的成分实际上跟人的指甲差不多。然而,所谓的“药效”却让犀角的意向消费群体更加广泛,甚至不局限于富人群体。这些非法贸易的需求不仅威胁着的5种现生犀牛,甚至连西伯利亚冻土下埋藏的披毛犀角化石也曾被走私“入药”。
本次盗猎案件的严重程度,也反映出对全球盗猎网络和非法消费市场的管制仍有不足。而这种不足,很容易对爪哇犀、苏门答腊犀等极小种群物种带来毁灭性威胁。
爪哇犀还有希望吗?
遭受重创的爪哇犀是否还能看到希望的曙光呢?
或许,我们还可以对这种坚韧的动物报以希望。
几年前,由中国农业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认为,更新世前的犀牛类群就发生过大规模物种灭绝,一些现存犀牛物种已经经历并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种群状态,它们也演化出了诸多适应小种群的特征。相较于古犀牛,现存犀牛物种的有害突变比例显著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现生的犀牛种群通过群体遗传选择,已经尽量清除掉了有害突变,以保证其小种群的健康。
生活在印度某个国家公园里的印度犀|Itsjustadeep / Wikimedia Commons
生活在亚洲的另一种独角犀——印度犀(R. unicornis),其保育案例也证明了犀牛的顽强生命力。上世纪初,印度犀也因栖息地被破坏、过度猎杀等威胁,种群规模一度萎缩到不足200头;但在印度和尼泊尔当局的严格保护下,今天的印度犀已经持续恢复到4000头左右。
在骤然损失1/3的种群后,爪哇犀正面临着比印度犀更严峻的局面,火山的不确定性也让保护工作无法徐徐图之,它的命运或许真需要仰赖一丝好运气。但在祈求天时地利的眷顾之外,尽快重振信心、查补保育工作的短板、更积极地推进种群恢复和异地种群引入工作,才是决定它何去何从的关键。
博物馆中的爪哇犀未成年个体的标本|Peter Maas / Wikimedia Commons
这也并非只需要印尼一国努力。打击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网络需要凝结各方力量,最终的目的也不仅为保护爪哇犀。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上,中国也曾有过爪哇犀、苏门答腊犀和印度犀的足迹,先祖铸就的铜器上也曾留下巨兽孔武的风采。或许,当它们最终走出灭绝的阴霾,也能再次回到神州大地,续写未尽的故事。
作者:一个男人在流浪
编辑:麦麦





 2024-06-21
2024-0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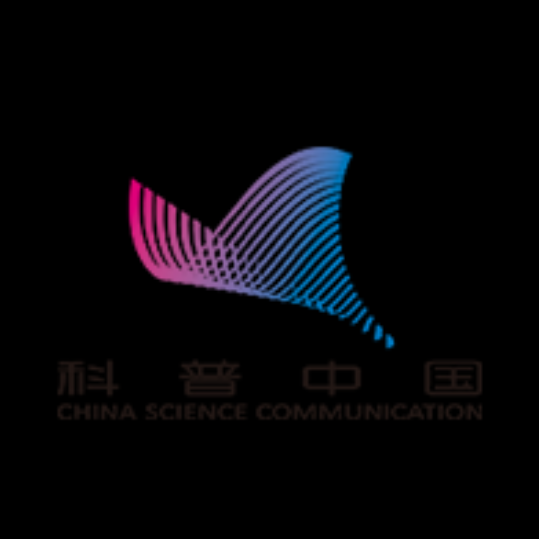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