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是美国著名推想小说家,是“新怪谭”(the New Weird)这一分支的翘楚。他的作品多关注科技对生态的影响,基于“怪异传统”(weird tradition)[1]47,突破时空限制,聚焦人类、非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反思人类命运,探索突破之道。
《异形博恩》(Borne)出版于2017年,小说展现了生化技术滥用的恶果,构想了非人类智慧主体的形象。学界现有研究集中于人类与非人类主体间的关怀和亲属网络建立问题、后人类视角下跨物种形象解读以及空间叙事问题。《异形博恩》体现出现代人类面对诸如跨国企业等不可靠实体时的无助[2],同时构建了“资本世”(Capitalocene)背景下异常的城市环境叙事,探讨如何建立紧密的跨物种联系[3],并探索提出更进步的环境观念[4]。作为一部“强烈反映我们当下的小说”[5],该作品揭示出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政治和人文方面深层次的危机和影响,通过并置人类、非人类与科技造成的灾难,试图重新定位后人类语境下的环境、生命和伦理关系,并讨论在面临共同性危机时需要采取的行为和价值准则。
《异形博恩》讲述了拾荒者蕾秋与生化怪物博恩在末世背景下的城市“恶托邦”中发生的冒险经历。曾围绕生化公司运作的某座无名城市,随着公司的衰落和关闭而凋敝,留下废墟、污染、生化怪物和无助的居民。拾荒者蕾秋外出途中意外在生化巨熊摩德身上捡到一个不明生化物,遂将其收养并取名“博恩”(Borne)。博恩通过吸收各种物质,肉体与智慧惊人地成长,同时对周围的一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最终蕾秋不得不将其驱逐出住所。同时,摩德持续杀戮破坏,自称“魔术师”的神秘人物也不断引起争端,掠夺地盘与资源,威胁着蕾秋和同伴维克的安全。当他们被赶出栖身之所并险遭杀害之际,博恩现身与摩德同归于尽,蕾秋也发现罪魁祸首是早已覆灭的生化公司。最终城市迎来和平,蕾秋和其他生灵一起努力重建城市,迎来新生。
当今世界面临众多挑战,包括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物种灭亡、瘟疫流行、人口问题、社会不公、政治经济冲突以及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6-7]。发达资本主义追求极致的利益,企图以机会主义和商品化的逻辑改造并掌控一切,导致了当前的后人类困境[8-9]。《异形博恩》的城市“恶托邦”正是其戏剧化的浓缩,映射出当下面临的生态、社会和道德的三重危机。
一、后人类时代三重危机叙事
(一)生态危机:环境、基因污染和生态失衡
生态环境是地球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生物和非生物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后人类语篇的核心是去人类中心化,涉及生态、自然环境的跨领域研究,构建了后人类生态批评和后环境研究的框架。人类曾通过干涉和改造自然,创造了优越的生存环境,拓宽了自身对世界的认知,促进了文化繁荣。然而,在以人类中心论为内核的资本主义驱使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干预带来了恶果——第六次大灭绝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而降临[10]。科技作为一种中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关系中遭到滥用,成为损坏、干涉和压榨生态及环境的帮凶,生态环境沦为“无自然生态”(Ecologywithout Nature)[11]。
范德米尔关注科技滥用问题,并在其作品中展示了生态破坏的普遍性恶果。《遗落的南境(三部曲)》(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以一起石油泄漏事故为灵感[12],《异形博恩》则将故事舞台放在一个遭受严重污染的城市中。主人公蕾秋和同伴维克居住的“城市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13]66,在他们的住所“观景崖”下,流淌着因污染而具有毒性的河流。这个世界的气候显然也已遭到破坏,水循环已被严重干扰。“流水多年前就消失,树木也都枯死了”[13]256,只有少量耐旱植物在沙化的土壤和沥青的缝隙里存活。博恩在日记中记录下洗澡的愿望,但井水干涸和海洋枯竭使他无法如愿。下雨也成为“稀少而短暂”[13]17的事件,“即使是真正的雨水,也往往有毒”[13]17,因此活物在雨天都不得不藏身起来,躲避致命的毒雨。所有污染与破坏的源头都指向资本主义经济下对技术的滥用:西北区的工厂烟囱制造出大量污染“导致了周边地区的毁灭”[13]103,之后,生化公司任由生化改造产生的毒素和污染不断向外扩散,直至影响到城市全域,成为“一切污染的源头”[13]291-292。
范德米尔同样对生化技术可能导致的遗传物质污染问题发出了警示。当代生态污染已涉及动植物和人类的基因安全。基于现代农业、畜牧业的商业需求,转基因技术实现了对多种动植物的基因表达和修改。尽管这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有助于缓解全球性的粮食安全问题,但也有学者表示担忧,转基因技术若不加以限制,会为自然界带来巨大风险和生物安全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耐药性、转基因堆积以及生物多样性紊乱问题[14]。当前,人类基因组编辑受到科学伦理和法律因素的制约,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禁止。然而,仍有超人类主义学者支持优生学(Eugenics)和非医学目的的“人类增强”(HumanEnhancement)。这一观点遭到了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对潜在危害的警示[15]。
《异形博恩》中的基因编辑导向了一种充满风险的狂野未来。对生物的生化改造并没有成就美好和谐的世界,反而驱使世界走向动荡不安。会飞行的巨型熊怪摩德原是生化公司雇员,他在被改造后失去了理性,只会无差别地屠杀;试图取代摩德的“魔术师”利用生物技术制造了人兽混合的部下;融合了动植物特征的博恩原本就是生化公司制造的武器。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一旦解除法律与道德限制,生化改造领域将爆发追逐利益的狂潮,对人类和其他事物构成致命威胁。讽刺的是,身为生化物制造专家的维克其实也是生化科技的产物,作为人造人,他形象苍白,依赖药物,体内寄生着诊断蠕虫,生化科技也无法让他拥有健康的体魄。科技无法创造出集健康、智慧和理智于一身的完美生物,反而加速了被改造者丧失主体性的进程:摩德和其他被改造者看似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跨越了生物和非生物的界限,但他们不仅短命,而且容易遭到控制和利用。维克只能依靠药物苟延残喘,丧失了对健康和生命权的主导;博恩虽然拥有智能并爱好和平,但饱受杀戮本能的折磨。这种主体性的丧失则进一步导致了个体的自我削弱以及与其他事物关联性的弱化甚至自我的异化,沦为科技滥用者的奴隶。
(二)社会危机:冲突激化,生产力下降
《异形博恩》中第二重危机体现在社会秩序的崩盘。首先表现为无序化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在当代利用意识形态灌输和数字技术塑造后阶级叙事[16],制造出“统治—被统治”的阶级鸿沟,其固有矛盾爆发必然导致统治秩序紊乱。如果没有进步力量的指导,资本主义的幽灵仍然会继续盘踞,使人民无法走出混沌。小说描绘的城市生产生活原以象征资本主义秩序的生化公司为中心,公司倒台后,摩德仍肆意横行,人类与非人类均无法重建秩序,导致城市陷入动荡。无论是暴君般的魔术师,还是暴虐的生化怪熊,在蕾秋看来“都很难让人接受”[13]174。因此,拾荒者只能隐蔽自己的气息,随时戒备,否则很可能像穿着防化服的三名“宇航员”一样横尸野外;前雇员们像流浪汉一样躲藏在大楼内,但最终难逃一死;蕾秋即便睡觉也穿着鞋子,随时做好逃亡准备。人类和动物只能借助黑夜隐蔽自己,因此博恩创造了“夜行国”[13]188这个词,映射出惶恐不安的社会氛围。
社会对抗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种对抗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表现为资源占有和奴役他人,小说中体现为地盘争夺、资源掠夺和剥夺自由。为了获取资源以保障生存,人际关系简化为敌友对立,武力冲突经常发生,冲突中的失败者沦为胜者的仆从。摩德、拾荒者和魔术师之间的地盘争夺又进一步加剧了混乱。栖身于各处的拾荒者为争夺必需品而战斗;魔术师则屡次攻击观景崖以获取对抗摩德的资源;摩德的代理①也数次袭击魔术师和观景崖来扩张地盘。困于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所有势力陷入了诉诸暴力的恶性循环。
因此,虽然科技高度发达,但在动荡的冲击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却依旧处于原始状态。一方面,生化公司彻底分离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使得居民无法正常进行物质生产;另一方面,在因严重污染而荒芜的环境中,居民无法开展农业活动,使得自给自足不复可能。大多数幸存者沦为拾荒者,像蕾秋一样,在毒素遍布和危机四伏的废墟里,靠着敏捷、经验和运气寻找维持生活的物资;而有些则像维克,利用技能处理生化资源以换取所需;少数人“学会了在自己身上培育食物供自己食用,但收成越来越少”[13]78。他们明白,以各种途径收集而来的资源,包括“很久以前取自生化公司的甲虫部件和其他必需品”,也“终会耗尽”[13]17。
(三)道德危机:价值扭曲、功利主义与人际信任缺失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道德溃败是《异形博恩》中的第三重危机。道德作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准则,同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个人修养和文化传承。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本,推动了资本主义繁荣,但由此发展而来的人类中心论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爆发,引发道德危机。蕾秋居住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其上层建筑受制于其资本主义本质。道德危机分别从阶级关系、个体价值取向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展开。
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雇佣行为催生了人身依附,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就好像是地位决定了人,而不是人决定了地位。”[13]312这种雇佣关系实为工人将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导致劳动者失去自由,资本再生产则加剧了阶级分化,并异化了劳动阶级。魔术师与其打手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关系。表面上来看,她提供了食物和庇护,然而“安全”与“自由”作为人类固有的权利,本不应被当作交换的筹码。同时,她索取的代价却极为沉重——手下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为她提供武力支持。魔术师也数次试图招募蕾秋和维克,其目的并非缔结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想利用他们的才智,占有观景崖里的物资。因此,这种具有资本主义内核的关系充满了掠夺性的剥削与压迫,制造了对立与矛盾。
这种社会环境加剧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和原子化,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出于生存和对抗孤独的需要,蕾秋与维克同居并保持亲密关系,但一直互有隐瞒,同时也相互打探。蕾秋一直无法把两人单纯地定义为一种简单的相互信任关系,他们时而是爱人,时而又是合作伙伴,但更是一种雇佣关系。在维克看来,“大多数感情都集中于生化公司里的人”[13]29,其多次被抛弃和被背叛的经历,使得他再也无法与人坦诚相待,哪怕对蕾秋也只保持有限度的信任。他们对于观景崖之外的人更是抱有警戒和敌意。随着社会网络的破碎,正常的人际交往也不复存在,个体成为孤立、碎片化的存在。
同时,资本主义过度追求利润与竞争的倾向,使得社会约束缺位,导致资源不合理分配,间接造成了社会资源匮乏和社会的无序化,并影响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城市中的金融体系随着社会秩序的崩盘而不复存在,拾荒者们更多选择原始的以物易物。然而,生化公司背后的资本主义物权观念仍在侵蚀着幸存者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的交换价值至上的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17]。这就导致一种逐利的机会主义的盛行,人们的行为都以利益为导向。另一方面,物质主义成为人们的主导观念,任何事物,甚至具有生命的个体都可能沦为可出售的商品,因此,不仅蕾秋的记忆片段被维克贩卖给了魔术师,甚至人类也成为交易中的商品。拾荒儿童提姆斯因年幼无法创收且消耗资源,被拾荒者群体视为累赘,被迫成为交易中的“货物”。幼年的蕾秋躲藏在货箱中时被运送到城市中,“按照公司规定……不算是人类,而是生化产品,是零部件”[13]333。即便魔术师认可蕾秋的才能,但仍然说她是“很有价值的货品”[13]140。大多数人面对生命冷漠无情,一味逐利,导致残酷且荒唐的事件一再上演。
在动荡催生的绝望中,一些人主动放弃主体性,将自主权让渡给集权主义,服从、赞美甚至崇拜权威。蕾秋在进入生化大楼废墟后,发现生化公司的幸存雇员为了生存而服从摩德,甚至形成了崇拜摩德的狂热教团,他们“用仅存的知识为摩德效力,罔顾一切”[13]312,制造出了大量熊怪协助摩德实施屠杀。丧失了主体性并随波逐流的个体,无形中成为权威的附庸与帮凶,也成为“米尔格拉姆权力服从实验”(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和“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现实写照。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心理学化统治”,自由独立的个体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改造成一种“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市民主体与心理学个体。”[18]因为实行杀戮行为的是摩德,而非生化公司员工,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合理且免责。但讽刺的是,幸存者们仍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摩德最终还是毁灭了他们全员。
二、后人类困境探源与消极对策解析
(一)探究后人类困境根源
在小说中,与末日城市废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蕾秋幼年所在的世界。通过蕾秋零星的童年回忆,读者可以窥探到一个祥和美丽且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那里享有生化技术改造的便利,生态也受到了较好的维护,虽然部分区域受到诸如海平面上升和难民问题的困扰,但和此处的城市相比,似乎是人间天堂。然而,当蕾秋在潜入生化公司的镜厅后,发现那个乌托邦竟然存在于时空传送门的对面。传送门的两端曾经存在大量而频繁的物质交换:对面送来材料与订单,在这里完成肮脏有害的生化改造,再将成品送回。当对面不再需要此处,便送来大量伪装成儿童玩具的“博恩种子”,意图利用生化武器毁灭一切作恶的证据。所有这些的幕后黑手皆是生化公司,它横跨两个世界,控制着一切,播撒绝望,剥夺了所有人“自主自辖的能力”,“深深嵌入我们的历史,直到永远”[13]327。
蕾秋最终并未受到“对面”美好景象的诱惑,她深知“它并不真实……无法解救我们中的任何人”[13]325,甚至“是个陷阱”[13]328,因为传送门对面的安宁祥和是以此处的污染和破败为代价的。为了造就彼处的繁荣,此处承受了产业转移带来的工业污染、生态破坏和社会混乱:生化废物池中的大量失败品如同“恐怖秀”,产业枯竭后员工遭到无情抛弃,人造的秩序仲裁者摩德走向失控,同时间接造就了狂暴的反抗者魔术师,以及在利益榨取殆尽后运送来毁灭城市的博恩种子。
范德米尔以资本主义作为蓝本进行虚构[1]52。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目的依然是谋求利润与剩余价值,并利用全球化将其势力渗透至其他地区,借由工业生产和经济交换,打造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资本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加重了世界的撕裂,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和二元对立的本性。正是这种对立性、抽象化的力量引发了当前后人类时代的重重危机。
尽管生化公司已经覆灭,但其遗毒积重难返。三重危机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摩德作为生化公司的终极产物却突然丧失飞翔的能力,预示着资本主义注定失败。然而,资本主义并不会自行消亡,铲除根源依然需要不懈努力。
(二)驱散消极迷雾:失败主义和暴力手段的局限性
发达资本主义试图剥夺支配对象的主体性,将这些对象他者化,并把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支配关系。但即便身陷于多重危机的困厄中,仍然有人怀有希望,追寻生存的意义。在乱世求生时,维克不忘提醒蕾秋去思考自己真正的生存目标,以防止蕾秋迷失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之中。同时,蕾秋通过与博恩讨论存在的意义,开启了对生活目标和生存意义的自省。虽然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开辟新秩序的努力,但并非均有收效,方向和理念的差异导致最终结果大相径庭。范德米尔呈现多种不同的选择,探索在后人类汇流(posthuman convergence)中突破资本主义体系性矛盾的行动指导,通过维克和魔术师的结局,排除了消极性行为所导向的失败道路。
维克代表的逃避主义注定导向失败。维克在遭到公司抛弃后,依靠制作药物和生化改造物谋生。他选择了与蕾秋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常年隐居于观景崖中。他常常沉湎于酒精带来的自我麻痹,依靠生化甲虫重播过去的美好记忆逃避现实,没有“酒泡米诺鱼和记忆甲虫,他就快乐不起来”[13]182,“每当有什么事让他想起关于生化公司的不快回忆,引发他那夹带着自卑的愤恨与忧郁,他都这么干”[13]12。他面对摩德的威胁和魔术师的通牒,在反复犹豫与延宕中放弃反击,不断加固观景崖,设置陷阱,视其为“堡垒”和“防御工事”[13]224,祈求能够偏安一隅。然而,观景崖还是无法抵御魔术师手下和摩德代理的频繁入侵,庇护所的毁灭逼迫他们走上逃亡之路。维克的选择证明了消极退让必然失败。
魔术师代表的以暴制暴的道路也被证明是无效之举。在混乱中崛起的魔术师,其行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对抗劲敌摩德,她驱使大量改造儿童作为暴力代理,却无视他们的心智丧失和病痛死伤。她认可蕾秋的机敏和维克的知识技能,希望得到二人助力并占有观景崖。但她却采取了胁迫的手段,通过折磨蕾秋来逼迫维克屈服,并利用维克的弱点发出最后通牒。然而,这条道路最终以失败告终,魔术师在与摩德的战斗中被驱赶至生化大楼内,最终死去。正如蕾秋所判断,魔术师“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迷失了方向”[13]323,她认为通过暴力获取权力是解决混乱的唯一途径。但暴力压迫注定无法成为新秩序的基石,围绕个体特权建立的秩序依然不稳定,因为这是一种根植于个人中心主义的霸权模式,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逻辑。在此基础上的短期和小范围的稳定的假象无法长远,因为依然会延续非此即彼的斗争,重入生化公司和摩德的歧途。
三、批判性后人类主义的伦理救赎之路
《异形博恩》中,蕾秋与博恩的选择向一种反对人类霸权、倡导万物平等与联系的后人类转向。后人类转向基于反人本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汇流,抨击将“‘大写的人’作为人类普遍代表的人本主义理念”,同时也“批判物种等级制度,推进生态正义”[19]。冲破具象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摆脱后人类困境,需要运用批判性后人类主义(criticalposthumanism)的理论框架,建立具有平等主义、横断性和肯定性的伦理观念。
(一)嵌入式的平等主义
摆脱后人类危机需要从根本上跳脱出资本主义认知和体制的束缚。温和的改良往往无法奏效,暴力革命往往必不可少。因此,范德米尔以暴力冲突推动戏剧性的高潮:巨大化的博恩与巨熊摩德展开终极对决,通过同归于尽的方式,让城市逃离生化改造巨兽的威胁。摩德代理、魔术师及其爪牙随之消失。至此,整个城市获得彻底的解放,迎来重建的希望。随后涤荡全城的大雨象征着城市所经历的革命,在大雨中“无论是被冲走的,还是新增加的,都有其重要意义”[13]349。
建立一个全新的、一元的和整体性的指导原则,能够扼杀霸权的萌芽,消解对立的源头。《异形博恩》所倡导的批判性后人类主义伦理,包含一种基于去人类中心化的平等主义理念。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块茎”(rhizome)理论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都展示了后人类主体的网络化关系,即位于网络中的每个主体相互紧密联系、相互平等,可以有效消解人类中心化。N. 凯瑟琳·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卡里· 沃尔夫(Cary Wolfe)、蒂莫西· 莫顿(Timothy Morton) 和罗西· 布拉伊多蒂(RosiBraidotti)等学者均明确反对启蒙运动以来主导一切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他们指出,后人类主体植根于自然环境,与周围的动植物紧密相连,并与技术交织在一起[20]。无论是地球、环境、非人生物,还是包括塑料、电线、细胞、代码和算法在内的“科技代理”[21],它们与人类在日常遭遇中建构出致密的纽带,发挥后人类主体的独特作用,成为丰富世界的重要力量。
蕾秋对各类人和物一视同仁,正是这种后人类主义的同理心(posthumanist empathy)的体现。这种同理心意味着,在承认后人类主体的个体性的同时,也要直面他们身上存在的、我们所不喜欢的部分[22]。面对博恩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怪物,她不带偏见地接纳他成为家庭成员,称呼其为“他”而不是“它”,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养育”和教导他,把他当作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当蕾秋检查博恩与摩德代理搏斗而留下的“伤痕”时,她意识到,与非人类打交道时,更需要跳出人类狭隘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地思考与共情。在阅读博恩的日记后,蕾秋认识到他一直挣扎在自己的杀戮本性中,原样接受博恩的本来面目则需要和他一起正视这种“属性”。因此,接纳博恩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关爱与伦理的建立。大战之后,蕾秋并没有利用权力的真空在城市中树立权威。相反,她选择回到观景崖继续以往的生活,并邀请其他人和生物入住,一同建设维护居所并修复环境。她的选择是对每个生命自主自决的尊重,表明了她努力与其他后人类主体建立起跨物种的价值纽带。
(二)横断性的普遍联结
充分认知并发挥后人类主体横断性特质的作用,也有助于构建批判性后人类平等主义伦理。后人类主体具有横断性的特质,表明所有生灵都各具特异性,相互密切联结与依存。运用横断性的概念和实践,有利于打破人类/ 非人类、自然/文化这类二元认知,有利于在后人类时代的危机中,破除资本主义二元化的对立思维和人类中心论,有助于以平等、非线性且网络化的方式发展与动物、算法系统和行星有机体的联系[23]。博恩是后人类环境中具有横断性的后人类主体,能够连接人、非人主体和科技,促进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当蕾秋首次发现博恩时,他“像半开半闭的海葵”,散发出“一阵阵海水气息”[13]2,“有点像海葵和乌贼的混合体”[13]5。当他与摩德决战之后回到休眠状态,散发着“盐、浪花和海藻”的气味,“像一株植物,吸收阳光中的能量”[13]356。随着博恩的成长,他能够移动、捕食蜥蜴并改变外表,甚至模仿蕾秋说话并自主交流。博恩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同时也有着多重感官。尽管如此,他仍具有其创造者植入的兽性,因此他早就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件武器而诞生的。由于蕾秋的平等且充满关爱的教育,他试图压抑自己的杀意,并愿意为他人牺牲自我。因此,他作为生化科技的结晶,集动植物特征于一身,同时在兽性、智能和道德感的角逐中,形成了复杂的自我,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也正是如此,博恩最终发挥了连接多方阵营,突破二元统治的重要作用。博恩的存在,是后人类主义与平等主义理想的体现,彰显了生物、环境和科技能和谐共存的理念。
(三)生成主体与肯定性的伦理
建立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和肯定性的后人类伦理,是医治后人类汇流中所激荡起的各种消极、负面与悲观的良药。这种肯定性的希望和对集体事业的追求是一种建立、维持和描绘可持续流变的战略,由责任感和代代相传的使命感所驱动,并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实践中[24]。布拉伊多蒂认为,肯定当下的生成力量,并借用将来的力量,对于促进这种集体性的进步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给予(他人)甚至自己都没有的东西”,即表现出一种大爱,一种“生成”(becoming)的力量[25]。肯定性伦理是一种结合每个实体的具体力量并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相互赋权的关系,旨在提高每个实体的个人能力,使其免受不利势力的侵害[26]。蕾秋基于这种准则的指引所作的选择正是这种力量的体现。虽然蕾秋仅有能力自保,但她对博恩这一充满谜团的非人生物却毫不吝啬地给予母亲一般的关爱。博恩展现出智能后,蕾秋一直以正面的方式引导他,对于“一块空白的石板”般的博恩,“只往上写有用的词语”[13]27,以塑造其正确的道德观,并一直试图帮助博恩抑制本性中的杀意。面对他人,她也不吝惜自己的善意。她尽可能避免暴力冲突,只在必要的时候自卫。当拾荒者首领意图卖掉儿童提姆斯时,蕾秋主动向拾荒者群体赠予物资,作为他们继续收留提姆斯的代价。
因此,经由与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及主体的多次遭遇,生成性主体得以形成,展现为一个嵌入式的、具体化的、关系的和伦理的过程[27]。小说从角色赋名和叙事视角深化了这一概念,博恩的命名即是对生成这一母题的回应。维克在谈及自己所制造的生化改造物时说道,“他的诞生其实是因为我赋予他生命”[13]19(“He was born,but I had borne him”[28]),蕾秋受到启发并因此命名为博恩。与“born”体现的被动(语态)不同,“borne”作为“bear”(出生)的主动语态过去式,体现出蕾秋和博恩积极进取的态度。他们身处危机中,没有被动等待希望,而是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创造理想中的未来。他们所在城市的匿名性使其可以成为读者所居住的任何一个地区的缩影,以蕾秋为第一人称视角建立的个体化叙事与读者的未来想象共鸣,投射出这种积极的生成体验的普遍可能性。在肯定性后人类伦理的主导下,博恩和蕾秋作为后人类主体的“生成”过程,及其带来改变世界的生成性力量,是点亮未来的希望。
蕾秋集坚韧、善良、宽容、高尚于一身,在困难中锐意进取,是范德米尔心中肯定性的平等主义后人类伦理的理想化身,博恩则证明了具有横断性的跨物种后人类主体的存在可能性。两者的形象塑造和并置,以及蕾秋与博恩的传承关系,体现了后人类身份定义的转向,即将传统理念中单一意义的“人”的定义拓展为后人类意义上的广义的“人”。蕾秋对博恩,以及博恩对自己后人类身份的确认,彰显了更广阔维度上的后人类政治。他们带有这种乐观态度,基于集体责任感,发挥肯定的平等主义的积极作用,是纾解资本主义及人类霸权造成的环境、社会和道德危机的良药。
四、结语
虚构类文学中的危机叙事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危机本身的映射与想象,更重要的是对危机根源的挖掘,以及解决危机途径的探索。《异形博恩》采用“环境启示录小说”的形式,投射出后人类时代的重重困境,试图引发读者对认知资本主义和人类特权思维的警醒。范德米尔通过想象蕾秋与博恩所经历的人类世多重危机和反乌托邦式全景中的冒险叙事,试图探索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伦理救济,激发读者对当下的思考,旨在推动对更美好、更多元的未来的创造。
通信作者:
廖全宇,南京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科幻文学等。
①小说中生化公司所制造的听命于摩德的众多小型熊怪。
参考文献:
[1] GUBACSI B. Birds,Bears,and Writing Humanimal Futures:An Interview with Jeff VanderMeer at the 75th Science Fiction WorldCon,Helsinki,August 2017 [J]. Fafnir,2018,5(1):45-55.
[2] CLAPP J. Jeff VanderMeer,or the novel trapped in the open world[J]. 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2021,62(4):414-427.
[3] ECONOMIDES L. Home on the Strange:The Queering of Place in Jeff VanderMeer’s Borne Books[C] // Economides L,Shackelford L(Eds.).Surreal Entanglements:Essays on Jeff VanderMeer’s Fiction. New York:Routledge,2021.
[4] LANE S.“ Love Your Monsters” Anthropocene Discourse and Green Psychoanalysis in Jeff VanderMeer’s Borne and The Strange Bird:A Borne Story[C] // Economides L,Shackelford L(Eds.). Surreal Entanglements:Essays on Jeff VanderMeer’s Fiction. New York:Routledge,2021.
[5] GORMLEY S.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 by Jeff VanderMeer,and:Borne [J]. Configurations,2019,27(1):111-116.
[6] KENNEL C F. The Gathering Anthropocene Crisis[J]. The Anthropocene Review,2021,8(1):83-95.
[7] LIGHT A,POWELL A,SHKLOVSKI I. Design for Existential Crisis in the Anthropocene Age[C]//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ties and Technologies. New York: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2017.
[8] BRAIDOTTI R.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ritical Posthumanities[J]. Theory,Culture & Society,2018,36(6):31-61.
[9] BRAIDOTTI R. Posthuman Knowledge [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9.
[10] BENYERA E. For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6th Extinction:Post-Anthropocene[C]// PICARD M,BRENCHAT-AGUILAR A,CARROLLT,et al. Wastiary:A Bestiary of Waste. London:UCL Press,2023.
[11] MORTON T. Ecology without Nature: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2] VANDERMEER J. From Annihilation to Acceptance:A Writer’s Surreal Journey[EB/OL].(2015-01-28)[2023-12-20]. http://vasbiasm.org/research-articles-annihilation-jeff-vandermeer.
[13] 杰夫·范德米尔. 异形博恩[M] 胡绍晏,译. 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
[14] TSATSAKIS A M,NAWAZ M A,KOURETAS D,et 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A Review[J].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7(156):818-833.
[15] FUKUYAMA F. Transhumanism[J]. Foreign Policy,2004(144):42-43.
[16] 牛霞飞. 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及危害透析[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7):68-76,108-109.
[17] 高广旭. 资本文明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共产主义新文明形态的伦理精神图景[J]. 理论探讨,2022(3):136-143.
[18] 王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心理学前沿进展[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51(3):5-15.
[19] 罗西·布拉伊多蒂,周伟薇,韦施伊. 后人类批判理论[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38-52,75.
[20] KUKKONEN K. The Self and Subjectivity:Why the Enlightenment Is Relevant for Posthumanism[C]//THOMSEN M R,WAMBERG J(Eds.).The Bloomsbury Handbook of Posthumanism.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20.
[21] BRAIDOTTI R. Posthuman Knowledge. [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9.
[22] SOUSA M. Biotech Animals and Posthumanist Empathy in Jeff VanderMeer’s Borne [C] //BAELO-ALLUÉ S,CALVO-PASCUAL M(Eds.).Transhumanism and Posthumanis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Narrative:Perspectives on the Non-Huma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2021.
[23] BRAIDOTTI R. Transversal Posthumanities[J]. Philosophy Today,2019,63(4):1181-1195.
[24] 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 [M]. 宋根成,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25] BRAIDOTTI R. Affirmative Ethics and Generative Life[J]. Deleuze and Guattari Studies,2019,13(4):463-481.
[26] BRAIDOTTI R. Affirmative Ethics,New Materialism and the Posthuman Convergence[M]//DI CAPUA G,OOSTERBEEK L. Bridges to Global Ethics:Geoethics at the Confluenc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Berlin:Springer Nature,2023.
[27] BRAIDOTTI R,HLAVAJOVA M. Posthuman Glossary[M].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8.
[28] VANDERMEER J. Borne[M]. New York:MCD,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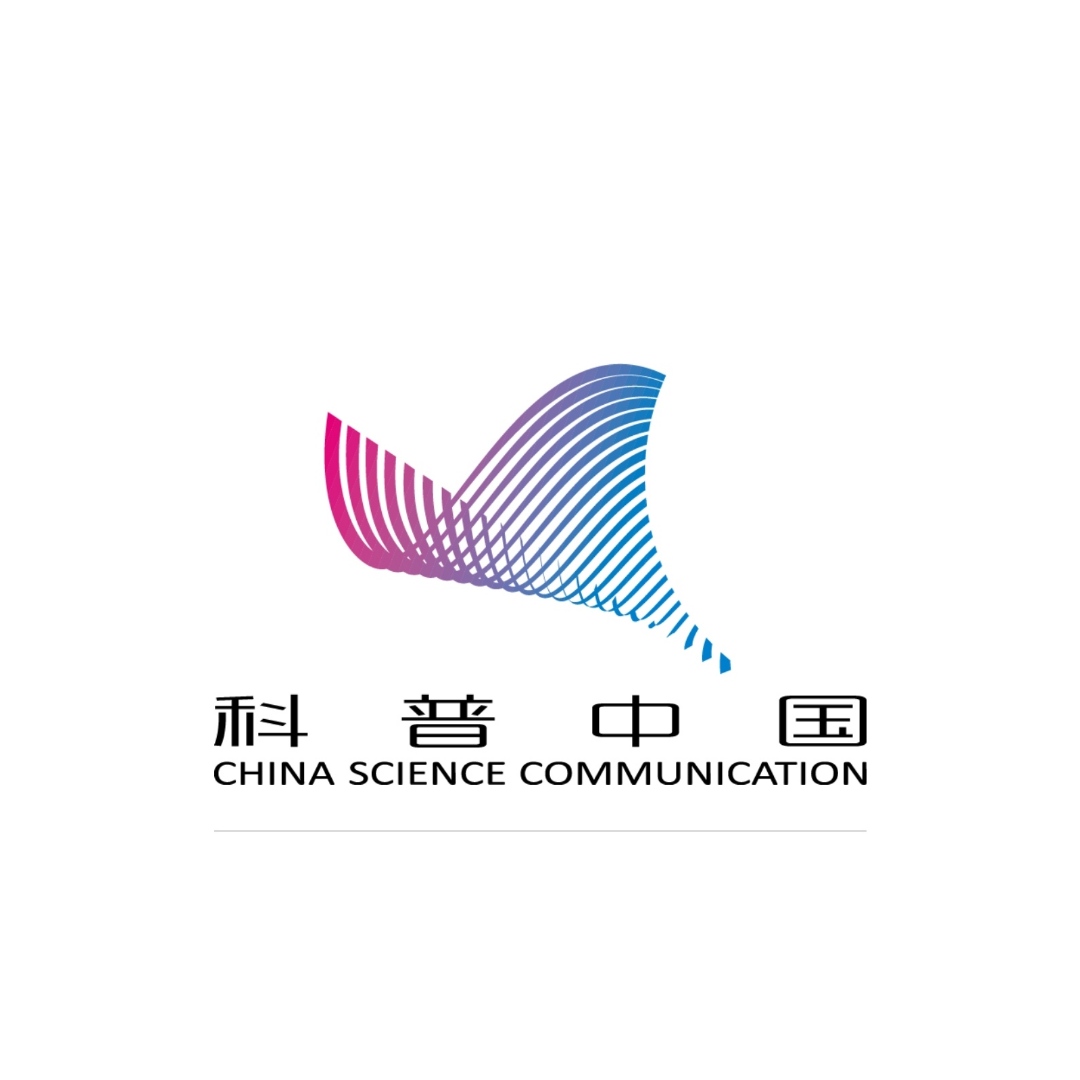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